作者: 发布时间:2021-11-11 15:52:41 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收藏本文
徐以骅:《宗教与2020年美国大选》,载《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4期,第130-1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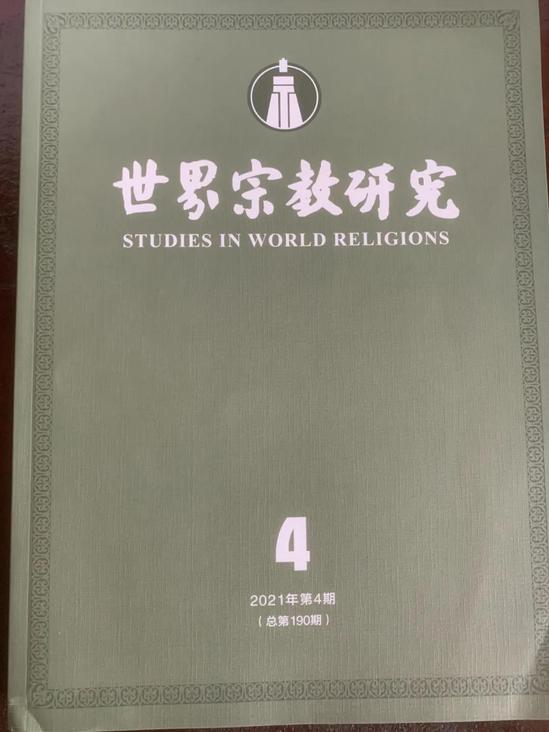
摘要:2020年美国大选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富戏剧性的选举之一,两大党候选人不仅在政治立场、执政理念和行事风格上大相径庭,而且在宗教归属和宗教倾向上迥然不同。并不笃信宗教的特朗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力于吸引基督教福音派的总统”,而在宗教右翼最聚焦的堕胎、性少数群体权利等议题上持自由派立场的拜登则以虔诚天主教徒著称。在本次大选中,2016年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的基督教福音派以及各种宗教保守派的神奇不再,再度引起了关于基督教福音派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甚至“白人基督教美国的终结”等话题。本文根据相关民调数据,对本次大选在宗教领域的基本特点进行分析,进而讨论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宗教遗产”以及大选后美国宗教政治的大致走向。
关键词:美国大选;基督教福音派;特朗普的“宗教遗产”
作者简介:徐以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宗教因素在美国大选史上扮演着程度不同的角色,而2020年大选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漫长和富于戏剧性的选举之一。实际上,在1800年、1886年、1928年、1960年、2004年以及2016年等几届大选中,基督宗教团体还具有十分显著且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次大选中,2016年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的基督教福音派以及形形色色的宗教保守势力的神奇不再,2020年大选是否能被界定为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政治上走下坡路的分水岭,也引起了各种分析。本文将主要讨论2020年大选中的宗教作用、民主党拜登获胜的宗教因素,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宗教遗产”。
一、宗教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
影响美国大选的因素很多,既有社会因素,如被认为对本次大选有较大影响的新冠疫情、经济、种族平等、堕胎、性少数群体、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环境保护、移民、犯罪与安全、外交政策等;又有身份因素,如一般政治选举通常会调查的性别、教育、地区、种族、年龄、家庭收入、意识形态(党派)等因素,而宗教只有影响政治选举的因素之一,其重要性通常不及经济、战争等社会因素以及种族、教育等身份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因素与其他因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很难通过民调准确地反映和判断宗教因素的作用,甚至确定哪些是“宗教选票”还是受其他因素驱动的选票。宗教在某次政治选举中发挥重要甚至关键作用,通常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如两大党在选举中势均力敌,宗教因素就有可能改变选情天平,决定选战胜负。正如长期研究宗教的美国政治学者约翰·格林(John Green)所言:“在竞选双方确实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几乎任何事都可以对输赢做出解释。”
二是在某些两党必争的关键州或战场州,宗教团体投票倾向的细微变化就可能产生放大效应,从而一举扭转选情,进而左右全国的选举结果。以上宗教作为选举终结者的两种情况较少发生,并且对其他很多因素来说也是如此。
三是政治候选人宗教立场迥异,并且强调宗教议题的重要性,把拉宗教选票作为主要的竞选战略,而宗教团体由于人多势众,并且能极大地煽动投票热情,其政治动员的能量是任何政党所不能轻视的。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共和党把自已扮演为“宗教党”,就是在经营某种宗教竞选或拉票战略,其杰作就是被称为“价值观选民年”的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这便使宗教右翼与政府当局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
美国关于宗教作为选举因素的选前和选后民意调查,在21世纪以来才有比较连续性的运作,其中有些民调机构如有“事实库”之称的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提供的连续5届总统选举中各宗教团体的投票率,就比较典型。2020年美国大选的两大党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不仅在政治立场、执政理念和行事风格上大相径庭,而且在宗教归属和宗教倾向上迥然不同。特朗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力于吸引基督教福音派的总统”,白人福音派则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而拜登是继阿尔·史密斯(Alfred E. Smith)、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约翰·克里(John Kerry)之后两大党提名竞选美国总统的第4位天主教徒,他不仅毫不掩饰其天主教信仰,而且“破天荒地将天主教信仰置于其2020年竞选运动的中心地位”。
美国学界对关于中期选举和大选的宗教民调的评价向来不高,美国宗教“万花筒”和“俄罗斯套娃”(即教外有教、教内有派)的属性,各民调机构采用不同的民调方法以及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致使各种民调数据有较大出入,甚至相互冲突,此种情况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尤为突出。由于新冠疫情催生的大量邮寄选票和人为制造的选举争端,关于2020年美国大选的各种宗教民调严重滞后,五花八门且差异较大,令人无所适从。
如上所述,就重要性而言,宗教团体在所谓战场州或关键州的投票率远胜于其全国性投票率。在本次大选中,一些宗教团体在关键州对拜登当选起了较明显的作用,如摩门教在亚利桑那州、基督教福音派在佐治亚州、穆斯林在密歇根州,以及天主教在宾夕法尼亚等州。尽管其中如摩门教和基督教福音派在总体上以较高比例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候选人,但它们在关键州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本宗教的全国平均水准,这便有可能使特朗普在这些传统“红州”败选,从而丧失再度入主白宫的机会;而无宗教归属者近数十年来日益发展为庞大的选举力量,并已构成民主党选举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这部分选民在各州影响力上升且以较大比例支持拜登-哈里斯组合的结论,在所有宗教民调中是最无争议的。
与20世纪末以来的宗教与美国大选政治的基本趋势相比,2020年大选中宗教作用的整体格局未变,局部则有变化;以基督教福音派为首的宗教保守势力虽然未能复制四年前的成功,但也并未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与其他选举现象相比,如特朗普赢得了向来作为美国大选风向标的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和爱达荷州但仍输掉大选,相对虚幻的宗教居然成为美国大选政治中相对稳定的因素。不过,本次大选也出现了一些预示美国宗教走向的若干趋势,这些趋势如继续发展则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改变宗教与美国政治的未来。
二、2020年美国大选的主要特点
从目前来看,尽管还有待更多相关数据的公布,但我们仍可较清晰地看到2020年美国大选在宗教领域出现的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宗教差距”的顽固存在
所谓“宗教差距”,即越信教的越支持共和党,越不信教的越支持民主党,是自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以来美国社会就已经存在着的政治与宗教互动景观,当年艾森豪威尔就获得了59%较为虔诚的宗教选民的选票。在本次大选中,根据各种民调至少有76%以信仰虔诚著称的基督教福音派投了特朗普的票,而且与以往一样,上教堂做礼拜的频率与对共和党的认同率成正比,而与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成反比。这种情况在天主教和摩门教信徒中也同样存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宗教虔诚度成了共和、民主两党选民的主要区别之一。然而这一“宗教差距”对大多数宗教少数派群体来说却并不存在。无论是黑人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他们的宗教认同率都比较高,大多数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或相当重要,但他们照样以较高的比例支持民主党和该党总统候选人。因此,所谓“宗教差距”只是对部分宗教群体如白人保守福音派才能成立,大部分黑人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是民主党的拥趸也同样构成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宗教政治的基本格局。许多虔诚信教的美国人支持自由主义议程,他们更关注社会正义等价值观而非宗教保守派崇尚的道德传统主义。“宗教差距”这一说法显然需要限定范围。
2.天主教徒选票的重要性,这也是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大选的一个主要趋势,再次印证了“得天主教者得天下”的说法。
拜登是虔诚天主教徒,平时很少错过主日弥撒,还经常随身携带表示天主教徒身份的念珠,被视为是自1976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当选以来最虔诚信教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但拜登在诸如堕胎、同性恋等议题上采取了越来越坚定的自由派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宗教保守派,在本次竞选初期的2019年10月还发生过南卡罗来纳州佛罗伦萨市圣安东尼天主教堂的天主教神父罗伯特·莫雷(Robert E. Morey)拒绝为拜登施圣餐的事件;拜登的竞选搭档、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 中文名贺锦丽)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艾米· C.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保守天主教社团“哥伦布骑士团”的背景穷追猛打,也引起部分天主教选民的反感。因此,拜登作为天主教徒在天主教选民中的天然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在宗教保守派的关键议题上的自由派立场所抵消。天主教作为移民宗教,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虽然该教在19世纪50年代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教会。20世纪60年代初,以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作为标志,天主教会开始登上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由于美国新教教会左右两翼的分裂和极化,天主教逐渐成为美国宗教的中间势力,并且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有显著的中间地位”。当年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其天主教徒的身份曾引起巨大争议。而现在天主教徒参政议政,置身于美国政治的高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有人形容说,对拜登而言,其获得选民支持的因素不在于他“天主教色彩过重”,而在于“天主教色彩不足”。目前,美国众议院连续3任议长以及联邦最高法院9位法官中的6位,都是天主教徒。但在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同时,天主教的政治立场也日趋多元化,从传统上倾向民主党开始转向共和党,在获天主教党员登记数量和政治支持方面两党几乎平分秋色,使该教成为近数十年来美国大选中最大的摇摆选民群体。本次选举的民调无论就高还是就低,各派天主教徒对拜登的支持率,都比4年前对希拉里的支持率有所提高,如白人天主教徒中57%投票支持特朗普,42%支持拜登;而在4年前64%支持特朗普,31%支持希拉里。在拉丁裔天主教徒中,67%支持拜登,31%支持特朗普。天主教徒以较高比率支持在一些关键议题上与其相左的拜登-哈里斯组合,再次表明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群体一样均非单一议题选民,以及一些天主教徒对教会训导的不同理解,而拜登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宗教身份,教皇方济各对社会问题(包括贫困、难民、环保等)的关注、对特朗普政府建造边境墙等问题的批评以及一度对“民事结合”的模糊态度,也舒缓了美国天主教徒尤其是天主教上层对拜登组合的反对意见。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在本次大选结束后即祝贺拜登当选,并号召美国人民摒弃前嫌团结起来。
3.共和党在争取包括宗教选民在内的少数族裔中取得了不俗的进展,这是本次大选最出乎意料的现象。
拉丁裔、非裔、亚裔、穆斯林等少数族裔尽管在总体上投票支持拜登-哈里斯组合,但与4年前相比,他们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在全国范围内,共和党候选人也借助少数族裔的选票在一些选区获胜。一些初步的选后民调表明,在本次大选中有超过1/3的拉丁裔、超过1/4的亚裔和超过1/3的穆斯林投票支持特朗普,均比2016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非裔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要低得多,但特朗普在非裔男性中所获支持率达到18%,比2016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据《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特朗普在全美各地所获的拉丁裔选票几乎都比4年前有程度不等的增长。在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尤其在一些拉丁裔聚居的县份,该族群几乎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特朗普,足以抵消拜登-哈里斯组合在两州城市地区的选民优势而有余,为特朗普在上述两州的完胜作出了贡献。本次大选中少数族裔尤其是拉丁裔对共和党和特朗普支持率的普遍上升受到关注,有论者认为少数族裔部分转向共和党及保守派政治主要是出于特朗普作为在任总统参选的优势,以及共和党经济政策更符合少数族裔的向上流动性、更强调经济发展而非社会公平等原因,而且他们中很多人也并不自视为需要摆脱白人控制的受压迫族裔。有研究表明,大多数拉丁裔自认为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新成员”,只有1/4的拉丁裔自认为是“有色人种”;而高达50%投票给特朗普的穆斯林选民也自认为是白人,因此声称代表少数族裔的民主党及其候选人对他们并无多大吸引力。有宗教学者则指出,这些选后观察和评论所忽略的,是普遍的宗教保守主义以及美国约1/4的基督教福音派是少数族裔等宗教因素,宗教保守派的主要议题诸如所谓宗教自由的公共表达以及堕胎等对他们也同样至关重要。事实上无论在得克萨斯还是佛罗里达,拉丁裔福音派的投票率都远远高于拉丁裔的平均投票率,从而使特朗普在选举中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佳绩”。本次大选所反映的少数族裔对共和党的某种转向以及宗教保守主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和党是否能够成为“多种族中产阶级政党”以及美国两党政治的未来,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4.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能量有所下降。
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基督教福音派在“道德多数派”、“700人俱乐部”、“宗教圆桌会议”、“基督教联盟”等旗舰组织的动员之下组织起来,与共和党长期结盟,驰骋美国政治舞台长达40年之久,先后使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乔治·W.布什和特朗普问鼎白宫,并且在特朗普任期内使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本次大选中,大多数民调表明,与四年前相比特朗普在基督教福音派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在本次大选中的助选能力,主要受到以下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人口学上的瓶颈。在过去40年里,基督教福音派在其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张的同时,也经历了信徒人数日益萎缩的危机。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10月发布的大型调查报告,2019年有65%的美国成年人信奉基督宗教,比10年前的77%下降12个百分点。其中43%的成年人是基督教徒,比10年前的51%下降了8个百分点;20%的成年人信奉天主教,比10年前下降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无宗教归属者占成年人总数的26%,比10年前的17%增长了9个百分点。因此该报告得出基督教在美国“正在迅速衰退”的结论。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的此种颓势在青年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928至1945年间出生的美国人(即所谓“沉默的一代”)中,84%信奉基督教,50%每周至少上一次教堂;在1946至1964年间出生的美国人(即所谓“婴儿热一代”)中,76%信奉基督教,35%每周至少上一次教堂;在1965至1980年间出生的美国人(即所谓“X一代”)中,67%信奉基督教,32%每周至少上一次教堂;而在1981至1996年间出生的美国人(即所谓“千禧一代”)中,只有49%信奉基督教,22%每周至少上教堂一次。随着年轻人的流失,几乎所有派别的基督教会都面临的信徒人数下降的局面。美南浸信会这一美国基督教的最大宗派教会在2020年6月报告说,该会信徒人数出现连续13年的下降,其2/3的教会成员到22岁时至少有退出教会一年的经历。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2008年,白人福音派的总人口占比为21%,而到2020年该比例已下降为15%。显然,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是以其超高的投票率来维系其政治影响力的。二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与特朗普政府的过度捆绑,正在逐步侵蚀该派的社会公信力。特朗普上任后几乎不加掩饰地推进宗教保守派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议程,被白人福音派视为“文化战争的英雄”和“有史以来最亲近宗教的总统”。但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保守主义社会政策,尤其是其煽动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系列言行,以及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上的拙劣表现,也加大了福音派内部的裂痕。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福音派正在重蹈半个世纪前自由派教会上层的覆辙,因过度热衷于政治而成为“缺少士兵的将军”,并为其盲目支持及附和特朗普政府而付出代价。基督教福音派内部对特朗普支持立场的松动,也为拜登竞选团队的宗教外联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4年大选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为缩小与共和党的“宗教差距”,开始“打宗教牌”,采取各种措施与共和党争夺宗教选民。在本次大选中,拜登任命福音派人士乔希·迪克森(Josh Dickson)主持其竞选运动的“全国信仰参与组织”,其竞选团队还喊出了与美国南部基督教领袖会议“拯救美国的灵魂”的组织目标相类似的“恢复美国的灵魂”的竞选口号。在其竞选运动中诸如“不是我们的信仰政治行动委员会”、“信仰2020”、“基督徒反对特朗普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为公共利益投票”、“亲生命福音派支持拜登”等宗教外联组织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动员众多宗教领袖为民主党站台,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两党在争取福音派甚至白人福音派支持方面的差距。在一些战场州如密西根州,拜登赢得了29%的白人福音派选票,比4年前的希拉里多获了15个百分点,即约30万张选票;而在基督教福音派占选民约1/3的佐治亚州,拜登所获白人福音派选票也多出希拉里16个百分点,即24万5千张选票,使拜登在该州以比特朗普多获约14000票艰难胜出,成为28年来第一位赢得该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本次大选拜登在争取白人福音派方面所取得的关键性进展,虽无法撼动美国宗教政治的传统格局,却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特朗普在拉美裔、非裔、亚裔、穆斯林等少数宗教群体中所增加的选票,成为其胜选的原因。
三、特朗普政府的“宗教遗产”
无论在世俗还是在宗教领域,特朗普都是十足的话题人物。就宗教领域而言,特朗普在其任内使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结合的紧密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为美国社会留下了一份颇有争议和引起分裂的“宗教遗产”。
首先,主要由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和天主教保守派构成的宗教右翼势力是“特朗普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共和党最重要的政治基本盘。针对特朗普竭力利用宗教助选,耶鲁大学宗教学教授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S. Gorski)甚至评论说他“不是在竞选总统,而是在竞选上帝”。在2016大选、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中,宗教右翼势力以超高的投票率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不仅使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入主白宫,使共和党在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时间内取得了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其间共和党控制参议院4年、控制众议院2年),而且通过任命法官加强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倾向,这便为以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为特征的特朗普主义的大行其道,提供了可能性。继被称为“价值观选民年”的2004年后,宗教右翼势力再度活跃于美国内政和外交舞台,这不仅成了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坛的主要景观,也是加剧美国国内族群、左右、红蓝、党派分裂和社会极化的重要原因。
其次,特朗普被某些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视为“有史以来最亲近宗教的总统”,其政府也是近百年来美国最突出的“以信仰为基础的政府”。小布什政府时期宗教右翼团体对政治的过度介入被称为“神权政治”,而宗教团体的“政治见证”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特朗普在赢得2016年大选后对宗教保守派投桃报李,不遗余力地推行其社会议程,迅速兑现多张竞选时开出的支票,部分实现了宗教保守派多年的夙愿,或至少提高了宗教保守派对特朗普政府的期望值,这包括恢复反堕胎禁令(所谓“墨西哥城政策”)、任命多名保守福音派人士和牧师担任政府高官、签署暂停7个伊斯兰国家签证和移民的总统行政令、任命3位保守派人士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200多位保守派人士为联邦法院法官,并且一再扬言要废止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取消从事政治等活动的宗教团体免税地位的《约翰逊修正案》,试图为宗教团体进一步介入美国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当然,特朗普政府在宗教领域的许多动作被批为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如不经国会,总统根本无法通过行政令废除《约翰逊修正案》,事实上该法案也并未被国会撤销;而特朗普经常鼓吹的要恢复公立学校祈祷的论调,也纯属哗众取宠的空谈。但特朗普政府比自威尔逊政府以来的历任美国政府与宗教势力走得更近、对两者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更直言不讳,并且有机会为宗教保守派做得更多,如其任内因法官出缺而得以提名3位保守派人士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也是不争的事实。特朗普为宗教保守派鸣锣敲鼓的抢眼做法与其个人远非虔敬的乖张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特朗普政府在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方面也动作不断,其中最著者有2018年至2020年间连续召开的三届年度“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2019年2月组建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2020年年中成立的“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2020年6月2日由特朗普签署的《促进国际宗教自由行政令》,以及一系列关于所谓宗教自由的法案尤其是涉华法案等。有美国学者就把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成立的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以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和“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同列为美国政府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的五大机构,其中后三个就是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建立的,这便使过去20多年来美国建立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机制的努力达到了新的高峰。在特朗普政府任内,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鹰派在政府中所居官职之高、国际宗教自由议题在美国外交议程中地位之重,以及美国地缘政治战略与对外宗教战略配合之紧密,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四,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虽未促成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但在本次大选中仍助其获得了美国总统选举有史以来第二多的选民票,使共和党在众议院比中期选举多获了9席,并且在参议院与民主党平分秋色,需要民主党副总统哈里斯的一票来打破两党在参议院的权力平衡。因此,2020年美国大选是否如某些观察人士所预言的那样是“白人福音派的分水岭”,甚至标志着“白人基督教美国的终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多年来美国学术界热炒的美国宗教左右两翼争夺美国社会文化发展主导权的“文化战争论”,或者与宗教撕裂互相推动的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和“部落化”,正在很大程度上以政党斗争的形式成为现实。共和党与民主党不仅在许多政治和政策议题上分歧巨大,而且在关于美国核心价值观和未来发展目标上也严重对立。在基层宗教选民等的压力下,共和党很难摆脱特朗普的阴影,以至于即使特朗普不再竞选总统,该党也将会继续推行某种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第五,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共和党上下几乎都对特朗普言听计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特朗普的党”,而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因与共和党的过度捆绑,也几乎变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膜拜团体。福音派通过福音派咨询委员会等机构接近了政治权力中心,但其“信仰政治化”和“特朗普化”的代价之一,便是其社会公信力的下降。随着拜登政府的上任,美国国内宗教政治的重心将再现小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过渡时所发生的从右向左的转移。宗教右翼势力虽仍将在美国的“公共广场”占有一席之地,但“基督教草根进步运动”将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大的影响力,而保守福音派在拜登政府任内的失势也是美国社会尤其是宗教团体的基本预期。宗教左翼的基层动员还远远不具备发动其激进人士所主张的、继美国内战后南部重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三次重建”的政治能量,但其在环保、贫困、种族、医疗保健、移民、女性、性少数群体等议题上的社会政治诉求,将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宗教右翼以反堕胎、反同性恋为标志的“性政治”,进入美国国内宗教政治议程。
第六,在对外关系领域,基于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上业已形成的两党共识和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议题对政客的政治安全性、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的战略考量、民主党政府摘掉“世俗主义和无神论政党”帽子的选举政治需要,以及美国目前所标榜的重视联盟的外交路线,民主党政府最有可能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及对华关系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领域继承特朗普遗产,延续甚至扩充前任政府以“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和“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为核心的所谓国际宗教人权建制,继续将宗教作为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战略的工具。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是,民主党政府将会以所谓人权外交框架来规范、兼顾和推进其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议程,并且更有可能将大国关系意识形态化,使中美关系受到来自所谓人权和宗教领域的双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