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龙 发布时间:2021-11-24 19:34:41 来源: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收藏本文
【导读】
本篇推送为《新闻大学》2021年第10期特稿文章第3篇。如需获取全文请参阅刊发杂志。
摘要
互联网的出现满足了人类沟通交流几乎所有的想象,民众获得了空前的表达、交往机会,但人类并没有因此在更高程度上达成共识,反而坠入到“后真相时代”“信息茧房”的陷阱。与之相伴的是,群体极化从小群体扩展到公众舆论层面,触发对抗,不断放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撕裂与分歧。本文尝试从对话理论这一视角出发,通过透视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及其原因,进而得出新的结论,提出重返对话是化解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重要路径。
一、研究缘起与核心问题
伴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互联网逐渐呈现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1]可见当前民众生活日益信息化、网络化,互联网已经成为广阔的表达、交往空间。每个个体均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对事件发表个人见解并转发意见和看法,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余慧、杨媛,2014)。互联网深度嵌入国家、市场、社会,并与个体生活连接互动,由此营造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异的抽象平台社会,这一趋向使网络空间俨然产生了一个具备“公共领域”性质的全新话语表达空间(张志安、吴涛,2016)。
然而,吊诡的是,虽然技术为人类提供了更多接受信息和交流的机会,但似乎并没有促进更高程度的共识,在“地球村”中,人类有着重返“部落化”的风险,选择对抗而不是对话,不断加剧社会的撕裂与分歧,“后真相时代”“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壁”……一系列新的阐释体系似乎都指向了共识与真相的消解,而针对智能媒体的声讨,几乎也都集中于算法偏向对上述分歧的放大。“数字鸿沟、商业与碎裂化、网民共识的缺乏以及不平等与非理性的对话环境”等因素的存在,让哈贝马斯等人所期望的“公共领域”未得而先失(魏明革,2012)。同时,互联网具备开放性、互动性、匿名性、弱规范性等特点,使得社会公众参与网络公共事件的对话呈现出不确定、不可控性的特点(薛可等,2014)。更严重的是,这一切还会激发网民在公众话题参与上的无序与暴力(胡正荣,2012)。
悖论的背后,恰是当代复杂网络舆论现实的映射。在诸如“医患关系”“转基因”等一系列议题上,互联网没有成就一个理性、包容、可理性沟通的协商空间,反而放大了现实社会的撕裂,网民在社交网络上迅速聚集成一个又一个的网络圈群,内圈中的互动固守己见,观点持续加强并形成群体中的极化现象。更严重的是,这种极化已经从小群体蔓延到公众领域,导致公共讨论和社会交往滑向无序混乱、虚假虚耗的网络喧嚣。不同圈群狭路相逢时,不仅没有建立观点的互动基础,推进共识的达成,反而引起对抗导致分裂,公共讨论缺乏底线逻辑和制度规制甚至走向“为反对而反对”的观点混战,中间的声音几乎消失。基于此,本文认为,当务之急,须着手解决网络空间中的舆论极化现象,以达成在更高程度上的社会共识,降低社会摩擦,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为回应这一现实问题,本文拟引入对话理论,以参与差异化议题引发分裂和冲突的网络用户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用户群体在网络极化冲突过程中的行动机理与背后逻辑,并针对性地提出化解路径的创新方案,以实现公共舆论治理中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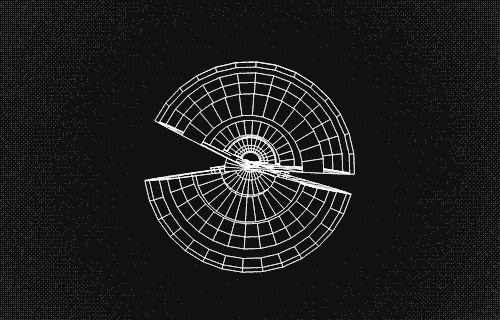
二、文献回顾
(一)群体极化研究的起源
群体极化不是一个新词,也不仅仅出现在互联网时代。20世纪60年代,群体极化现象就引起了美国学界的注意。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斯通纳(Stoner,1961)在进行一项关于小群体决策的研究时,意外发现群体在针对某一问题讨论之后,相应的意见或所进行的决策会比之前变得更为冒险甚至激进。詹姆斯·斯通纳选择使用“冒险性偏移”(risky shift)来解释这一现象。由于和当时社会心理学对群体决策的传统研究结论不同,该项研究激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该文也被认为是群体极化研究的起源。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研究者发现,经过群体讨论之后不仅会造成“冒险性偏移”,也会加剧谨慎性倾向(cautious shift)(Stoner,1968)。在此研究基础上,莫斯科维奇和扎瓦洛尼(Moscovici & Zavalloni,1969)认为,经过群体讨论之后,无论是发生冒险性偏移,还是谨慎性偏移,都描述了群体意见/决策发生的偏移,为此他们提出用“极化”(polarization)和“极化效果”(polarization effect)来统一定义。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群体极化概念,但是他们的研究启发了后来的学者。
科林·弗雷瑟等(Fraser et al.,1971)更进一步将“群体”和“极化”两个词合在一起,首次提出“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概念,并明确指出“群体极化”比“XX性偏移”更适合被用来解释群体讨论之后产生的意见/决策的偏移。在心理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群体极化”一词的概念形成并逐渐清晰化,具体被定义为:经过讨论之后群体集体所呈现的态度平均值,会比讨论之前变得更具极端化(Myers et al.,1976)。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学界已经形成了两大相对公认的解释理论(Isenberg & Daniel,1986)。第一种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theory)。个体在群体讨论中有着确认自我认知和被群体接纳理解的要求,因此需要不断比较群体中其他个体的观点并修正自己的观点,以使自己的观点逐渐向群体大多数的意见靠近。该理论也被认为是群体内的对话缺乏真正的辩论,个体只要接触到不同观点就主动迎合或者被裹挟,导致群体观点相比讨论前进一步极化(Teger & Pruitt,1967)。第二种是劝服性辩论理论(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theory)。群体讨论中的所有观点及论据都会呈现在成员面前,群体成员通过对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识别来完成群体观点的正转向或负转向。在这一讨论过程中,更具说服力的论据将决定讨论后的群体观点是发生进一步偏移,产生群体极化现象,还是朝着与讨论前观点相反的方向偏移,转向化解群体极化(Kaplan,1977)。
现实对话中,这两种理论状况常常同时存在的,两者都承认群体成员在对话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理性,并且这种对话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共识的言语交往活动(蒋忠波,2019)。然而现实却是,在很多情况下,群体讨论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而是停留在虚假的、强迫的或者系统扭曲的共识。显然,在线下对话的过程中,有太多影响因素,让群体极化成为理性对话的一个难点。

(二)国内外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如何解决传统社会沟通中群体极化的难题?互联网被寄予了厚望。然而如前所述,互联网给了人类更多平等、自由的对话可能,却演化为群体极化放大的“黑科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网站的兴起,网络中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认为,网络是群体极化的温床,具有同质观点的群体在经过讨论之后,相比一开始的态度会更加极端,并且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上发生的比率是现实生活的两倍(凯斯•桑斯坦,2003:41-47)。斯皮尔斯等(Spears & Lea,1991)通过研究发现,与面对面交流的群体相比,使用计算机交流的群体在决策时更容易产生极化。谢俊霖等(Sia et al.,2002)和麦克劳德等(Mcleod et al.,1997)通过对比实验,一方面确认了斯皮尔斯的推断,发现使用视觉隔离或者匿名化的讨论会加剧群体对话时的观点极化现象;另一方面,也发现网络匿名性可以增加群体少数派的机会,但也可能会削弱意见少数派在群体对话时话语表达的影响力。
国内学界对网络群体极化的研究较晚,郭光华(2004)是较早一批关注群体极化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网络催生了新型舆论主体——网民,并且由此聚集的网络群体呈现出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点,极易导致群体内部高度认同的现象。乐媛、杨伯淑(2010)则从中国网络论坛中的小群体讨论着手研究,发现在温和派占据主流的论坛中进行的群体讨论,不会出现观点的极化,而在激进派占据主流的论坛中,则更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因此,他们认为群体极化现象与讨论的议题有关。2012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公众“被激活”,并被挟裹进网络社会中,研究者逐渐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移动平台,开始对公众领域的群体极化进行了研究。辛文娟(2014)对微博中“武大赏樱门票涨价”事件分析后发现,争议性的话题和微博独特的传播机制,是形成网络群体极化的基础。陈福平、许丹红(2017)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中虽然存在有许多观点,但是不同意见群体之间的链接是封闭的,由于群际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群体极化现象发生。黄河、康宁(2019)通过选取今日头条、腾讯新闻、微信、微博四个平台中关于“江歌案”的全部媒体文本和网民发言,研究发现,群体极化现象是由在争议性事件刺激、自媒体煽动、专业媒体引导失灵等因素交互下产生的。杨洸(2020)从网络情感传染的角度分析,认为网络社区中的各类可见内容是影响网民参与和情感极化的重要因素,群体中某一成员的情感表达会传染到其他成员,并形成多次“反射”,最后推动同一极向的情感状态。
除了基于中国网络社会的经验层面研究,一些学者也尝试从理论层面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叶宁玉、王鑫(2012)通过分析近年来的公共事件,探讨了群体极化的积极和消极效应,并指出媒体和UGC优势互补,将会使群体极化现象走向积极一端。董玉芝(2014)认为网络群体极化对社会有正负效应,根据对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及原因的分析,提出通过政府、网民、网络媒体和立法等多方面的力量,来规避群体极化负面影响的建议。魏永征(2017)认为,虽然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不可避免,但通过信息和事实的及时呈现、不同意见的坦诚交锋和权威主体的及时引导,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极化的。夏倩芳、原永涛(2017)分析了对群体极化在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学中的概念差异,并指出了当前群体极化研究从群体心理到公众意见的研究取向的转变。蒋忠波(2019)从国内针对群体极化的研究偏差出发,对群体极化的概念形成、含义、是否理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梳理和辨析。

(三)对既有文献的检讨
目前,国内外针对群体极化的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视野从小群体决策逐步扩展到公众舆论方面,学术脉络也从社会心理学扩展到新闻与传播学、政治学等更多领域(夏倩芳、原永涛,2017)。国外群体极化的研究,在心理学领域主要集中在验证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存在与否,以及成因的探讨上;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体极化现象是否产生,以及具体的影响因素上。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研究在去群体极化或者促进负面群体极化向正向、理性网络交往方面的关照相对较少,这也是本文希望有所突破的地方。
网络群体极化的研究虽然从小群体群内决策逐步转向群际沟通下的公共舆论的研究,但就当前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还是主要着眼于群体内部的极化研究,缺少对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沟通效果的有效关注,而这一领域恰恰是对于解决对抗、达成更高程度的共识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小群体被认为是大社会的缩影(西奥多·M.米尔斯,1988:2-3),由此群体意见也就构成了公众意见的基础,群际之间意见的统一也有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然而,不计其数的“信息茧房”“过滤泡泡”造成了社会形态的严重碎片化,群际的封闭导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而这才是公众层面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
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将结合中国过去10年社交媒体与智能媒体兴起后发生的诸多群体极化案例,将关注的重点从通常的仅仅关注群体内决策影响机制扩展到群内对话与群际对话的协同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讨论网络群体极化的诱致因素与化解之道。

三、基于对话视角的讨论:网络何以会放大群体极化?
自人类诞生之初,对话这一行为就根植于人类文化生活传统之中,是人际之间最基本的交往形式,有关对话的哲学思考最早可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产生于们的对话交往过程中,而非来自于某个参与对话个体的头脑里。除此之外,苏格拉底还将对话应用到教授知识之中,基于“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步组成的“产婆术”式教学方法,利用对话来引导学生依靠自己的思考发现真理(蒋叶红,2017)。他关于对话的思考也影响到其他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重要著作均采用了对话的论述方式,到后来对话成为西方思想家的重要探索主题。视野转到东方,“对话”相关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周人的“礼”“易”学说,其中“礼尚往来”“阴阳互须”的思想确立了在中华民族人际交往中的“对话”原则。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崇尚的和谐对话促进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孔子的启发式教育和采用对话体的《论语》,老子“道”中蕴含的对话交往思想,以及庄子等其他先贤的思想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对话”理念的认可与诠释(张再林,2002)。
到了现代,理论家和哲学家马丁·布伯是第一个真正展开对话关系研究的学者,也被认为是“对话理论之父”。1923年,他在享誉盛名的著作《我与你》中提出,工具性的“我与它”关系并不能帮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只有当关系基于对话的“我与你”时,才能实现人际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理解(马丁·布伯,2018:1)。沿着马丁·布伯的哲学思想,米哈伊尔·巴赫金进一步把对话理论上升到社会思想层面、“主义”和哲学层面,将对话发展成一套有关“人的生存、存在、思想、意识的交往、对话、开放的体系”(胡百精,2018:124)。巴赫金关于对话理论的“复调”“狂欢化”“双声性”等概念范畴受到广泛关注。他认为在“狂欢化”的对话中,应该抛开人际之间的关系限制壁垒,消除话语霸权,让群体中的每个人自由言说,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找到自我并超越自我(钱中文,2009:45;董小英,1994:340)。同时代的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对话是一种“视域融合”,由于每个人背景不同,导致每个人在观点或“视域”上不同,通过对话的交互作用可以完成人与人之间的“视域融合”,来促进“理解”(何卫平,2001:380)。在对话理论研究领域,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沟通和交往是社会进化的重要动力和发展形式,一切重要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对话”中完成解答,通过建立理想话语情景,以“主体—主体”的平等对话关系替换以往基于“主体—客体”的支配关系,培养交往理性,再造公共领域,重建生活世界(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10-252)。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现代对话理论已经从人际传播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视角切换到互联网时代,对话理论不仅被视为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一种重要支撑方案,也被认为是其他方案实施的基础手段(胡百精,2014:258)。胡百精认为,从技术、理念和实践上看,互联网宣告了对话时代的来临,并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媒体、公众等多元主体的网络公共空间,以此实现对公共传播的认同、共识与承认。无论是小群体决策,还是进入公众舆论领域的网络交往,基本都是一个对话的过程。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于信息发布、说服或者宣传等其他传播概念,理性对话意味着双向沟通,多元主体参与进行平等地沟通,实现利益协商和价值分享(胡百精、杨奕,2016;胡百精,2014:82-120)。从对话理论的内涵来看,对话对于达成共识是如此重要,但对话却常常让位于对抗,从而造成在事实层面的真相无法还原、利益无法补偿、价值层面上的信任无法重构,这反过来进一步消解了对话基础,损害危机社会中有效共识的实现与维系。接下来,本文结合对话理论来讨论群体内外对话意愿被消解的诸多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

(一)群内有效对话机制的缺失:情感驱动的观点感染
1895年,互联网还未诞生,社会群体内部对话的手段和信息量非常有限,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断言,情绪传染在任何群体中都存在,不仅对群体的特点形成起着关键作用,还决定着群体的集体选择。其中,基于感性和本能的情绪相比基于理智、冷静的情绪更容易起作用(古斯塔夫·勒庞,2016:29-50)。历史的时针拨转到21世纪,情况似乎更加严重。当某一热点议题出现在互联网上,不仅能唤起用户的特定情感,而且借助网络的无限链接能力,网民可以围绕某一议题迅速找到观点相同的彼此,凝结成一个群体进行讨论和交流。特别是当遭遇敏感议题时,群体中的个体很容易受到情绪的感染或暗示,转到某一特定方向,失去个性和理性思考,甚至会做出与原本性格习惯相反的行为(黄河、康宁,2019)。
对立观点并不必然造成群体极化,但当对立双方存在明显的情感抵触时,则为极化构建了天然温床(Lelkes et al.,2017)。互联网满足了网民对于社会认同、情感支持方面的需求,方便人们找到基于相似“情感/情绪”群体的同时,还重新构建了群体中个体的情绪表达和关系(乐国安、薛婷,2011;开薪悦、姜红,2019)。现在,越来越多的亚文化及边缘群体加入到网络话语的构建中,由此产生的多元话语必然对主流话语产生强烈冲击(吴靖,2013)。有学者认为,当前公众舆论呈现出“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等特征,话语表达中掺杂着强烈的怨怼情绪,于是当公共事件进入社交网络中,就成为引起群内极化、群体对立的话语载体(张华,2017)。桂勇、李秀玫、郑雯等(2015)在研究网络极端情绪时也发现,社交网络时代的公众参与多为表达性参与,结果很容易导致公众的情绪化争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如何借助情绪的力量促进群体内产生有效的对话,是解决群体极化的重要途径。

(二)群际对话前提的消解:信息共享机制失灵
1.主流媒体的失语与商业新媒体平台的情绪诱导
胡百精(2018)认为,在危机传播管理的过程中,一方面,媒体要于事实之维还原真相,补救利益;另一方面,媒体也要于价值之维恢复信任,重构情感、态度等价值意义。因此,在对话过程中,还原真相构成各方实现有效对话的基础。然而,在“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生态中,新闻与事实之间的纽带正在断裂,经过无数次“再阐释”,信息的核心已经不是事实,变成了裹挟情绪的观点与立场,成为个人或自媒体强化某种偏见的对话论据。
这一社会问题的发生,对大众传播媒介提出了更高的传播要求。媒体不仅要在事实之维完成真相的披露,更要进一步满足网民在价值之维的需求。然而,当前主流媒体在这方面的引导是缺失的,在更关注情感和立场的当下,实际上是将真相的解释权让给了由无数自媒体组成的平台型媒体。同时,针对社交媒体的研究发现,目前社交媒体更多扮演了信息汇集的角色,而不是对话平台(Small,2011)。网民虽然能在平台上接触到多元化的意见,但是这种接触并不能引发有意义的讨论,增加的是具有相同观点群体的认同(Yardi & Boyd,2010)。相关研究发现,情绪加快了观点在网络上的流动,相比普通内容,充满情绪的内容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被转发更多的次数(Stieglitz &Linh,2013)。
2016年,关于《疫苗之殇》的网络大讨论中,起初仅仅是自媒体为了获得更大的关注度,采用不客观的新闻表述、夸张式报道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最终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恐慌。此后,主流媒体虽然跟进,对过期疫苗的危害进行了澄清,但依然未能完全解决舆论的混乱(董天策、班志斌,2016)。主流媒体科学、权威的解释性新闻并没有及时抵达网民手中,也让包含情绪性、煽动性的自媒体推文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信息共享机制的失灵,使得公众对话变得无从谈起。

2.“千·人千报”:算法导致用户关于世界镜像认知的“碎片化”
众多研究者认为,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公众对互联网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普遍存在,这一理论也由此成为当前群体极化研究的重要切口。选择性接触理论表明,人们对于信息的接收并不是全面的,多数人只选择接触和自己倾向一致的信息,而拒绝接触与自己观点、态度不一致的信息(刘海龙,2008:168-171)。由于网络信息已进入大爆发时代,以搜索技术和推荐算法为主的个性化信息技术不仅为信息分发和接收提供了便利,也为网民选择性接触信息提供了更好的工具。有学者研究发现,网民选择性接触会导致在信息接收上的同质化,一方面,这样常常会导致单一个体在观点上的极化;另一方面,也会使得阅读具备同一观点或立场的网民聚集起来,形成“偏见共同体”(Dandekar et al.,2013;黄河、康宁,2019)。通过算法识别出用户的选择性偏好的基本构成,并基于用户信息需求最大化的营销策略推动了“千·人千报”的精准化信息推送。从商业演化的维度来看,这是市场力量降低损耗,提高目标市场识别精度的一次巨大飞跃;但从社会共识的达成来看,对世界镜像认知的严重碎片化却使人们失去了对话的事实基础。
大众媒体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公众讨论问题提供基础性的事实,并通过权威话语整合公共多元化的态度和立场,以此达成公众对于事实在认知层面上的某种基本共识。在全新的传播模式下,当前这一“事实的一致性”不仅有着被“千·人千报”这一极端细分化市场策略消解的巨大风险,也有导致公众舆论滑向“碎片化”的危机。刘擎从尼采的“视角主义”研究出发认为,“没有事实,只有阐释”。对于“事实的一致性”的认知,依赖人们“共同视角”的诠释,而算法有着固化人们既有价值观和立场的倾向,同时还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群体之间对某一事件的视角分化(刘擎,2017)。当人们的认知被“算法”分裂成一个个碎片时,面对某一事件就会出现共同“视角”的缺失,当人们的认知出现偏差,即使接收到事件的真相,固执己见也不可避免。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快速传播的各种谣言和虚假信息,以及多种对于疫情防控的解读,给公众带来了在信息感知和理性判断的混淆。疫情当中,算法将媒体或政府的等发布的公共信息及时推送到网民,减少了不同群体面对新冠病毒防控的认知偏差,为重建大众传播整合舆论的功能构建了基础。用好算法推荐,或将成为减少群际之间对话分歧的有力工具。

(三)群际对话的数字“鸿沟效应”:“圈层离散”引发的舆论对抗
进入社交网络时代,主要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线下圈子,发展出新的内涵,兴趣爱好、价值观、职业等因素成为新的联结纽带(郑欣、朱沁怡,2019)。“圈层”一词最早来源于人文地理学科中的“圈层结构理论”,主要指城市经济发展呈现出逐渐由中心向外拓展的圈层化形态(张亚斌等,2006)。后来,这一概念逐渐延伸到人文社科领域,桑斯坦提出网络交往的圈层化(凯斯•桑斯坦,2003:37-55)。彭兰(2019)认为,在网络社会中,“圈层化”包括“圈子化”和“层级化”。一方面,圈层以某种规范或潜规则对个体进行约束;另一方面,由于信息被限制在同质化圈层中难以“出圈”,导致不同群体产生态度和立场的分歧,甚至对立,导致公共对话的消失。
以社会阶层为纽带组成的网络圈层为例,当面对一些网络舆情热点时,不同阶层的人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常在观点和立场上发生冲突。究其原因,线上冲突来自于深刻的社会问题。根据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显示,通过对微博上多种职业和多元社会群体的网络用户跟踪分析发现,当前网民最关注的12项议题分别为:教育、反腐、环保、房价、医疗、宗教、食品安全、民族、收入分配、养老、就业和户籍,这与现实社会网民所关注的网络议题基本相同。由此可见,网络已成为民众表达观点和情绪的主要渠道之一(李良荣、方师师,2018:112)。
以“阶层化”和以“圈子化”为联系的圈层化,都对个体存有规范和针对其他群体的区隔。当人们身处于“同味相投”的舒适圈中,越来越多的内容构建起阻碍个体与外界交互的圈层,让身在其中的个体感受到“我们-他们”的区分,陷入相似的观点和思维方式里,而无法理解其他圈层运行的逻辑。[2] 因此,冲突将不断加剧,导致一个个彼此离散而又封闭性的圈层化传播群体,成为群际对话中不可逾越的“数字鸿沟”。这也在提醒我们,化解不同圈层之间的隔阂,将有助于构建能够有效对话的公共话语环境。

四、重返对话: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化解路径探索
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群体极化现象的化解路径表现出“独白”的特征,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点对面的传播来提高社会各个群体在事实层面的一致性,进而为价值层面的一致性奠定良好基础。但是,在一个大众传播资源日益“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流动生态中,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认知与价值层面上的统合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众声喧哗中,如果人人拥有的“麦克风”之间各自停留在“独白”而不是“对话”状况,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带来的优势无疑被严重削弱了。乔纳森认为,在对话过程中,“讲话者”需要采用客观、合作、平等、开放、诚实、真挚、移情的态度来对待他人,不要轻易做出判断(Johannesen,1990;转引自陈先红,2018:139)。班纳特·皮尔斯等人把对话理论应用到公民社会领域,并提出“对话的精湛技巧”概念,具体包括:(1)对话是具有特定“规则”的传播形式;(2)这些规则使得人们愿意交谈,也愿意倾听别人的观点;(3)参与对话的人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对持不同意见者保持平等、开放的态度;(4)对话能力包含响应他们对话请求的能力、继续邀请他人对话的能力、构建适宜对话环境的能力;(5)对话能力是可以学习的,并且是有感染力的;(6)促使对话发生的环境有赖于有技巧的促进者,如果促进者离开,对话环境中的参与者将无法参与对话(Pearce et al.,2000)。就对话理论提供的解题方向来看,基于认知、情感、理性的三维价值目标的实现,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化解路径探索可以体现在“共享”“共情”“共识”三个层面。
(一)“共享”:扩大公共信息,重建有效对话的前提
如果说对话是共识达成的必经过程,那么充实有力的公共信息则是公众实现理性认知和有效对话的必然前提(石永军、龚晶莹,2020)。信息共享对于促进公众对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共享的范围有多大,对话的范围就有多大,共享的质量有多高,对话的质量就有多高,这对于信息的接受者公众和信息的传播者来说都尤为重要。事实既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也是人们决策之前参与社会讨论的前提,主流媒体作为新闻事实的“守门人”,在舆论引导方面具有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理应承担起向全社会提供信息共享的职能。很多情况下,群体极化的原因正是来源于信息披露的不及时,公众未能在主流媒体上得到及时完整的信息,出于对事实真相的信息需求,轻信平台媒体及不专业自媒体的引导。因此,主流媒体应该坚守新闻报道的价值导向。主流媒体对公众负责和对事实敬畏,把握新闻报道的三个面向:第一,在新闻报道上注重真实、真相、真理,反映客观世界的变动;第二,在对公众的基本态度要公开、公正、公平,不故意隐瞒事实,歪曲事实真相;第三,在新闻报道时空上要注重深度、广度、速度,争取实现与事件进展的“零时差”“零距离”(李良荣,2020:320-32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基于算法的智能媒体也是媒体的一部分,作为网络社会的重要节点,不能完全被“千·人千报”的精准营销迷惑,应该承担起更多公共信息的传播职责,在基础性公共信息供给的基础上,再寻求细分化的独特需求,而不是在推动社会关系碎片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自媒体作为新媒体环境下新型主流群体发声的新阵地,已经成为当前绝大多数热点事件的策源地,并有力推动着舆论事件的演化,要注意遵守传播伦理,不能过分追求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应该与主流媒体一起建设健康有序的互联网空间(李良荣、郭雅静,2019)。
另外,作为信息的接受方,网络群体需跨越非理性的认知鸿沟,尊重网络对话的基本伦理。群体极化中非理性信息流瀑现象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个体缺乏提出异见的勇气,过于沉浸到群体的话语场中。在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来临时,数字鸿沟带来的公民素养失衡一览无余。在面对危机事件时,公众必须增强自身的媒介素养,这样才能理性表达观点,真正促进共识的达成。

(二)“共情”:以情感沟通情感为纽带,突破群际对话鸿沟
进入互联网时代,情感已成为当前新闻业态的重要概念,情感表达比以往更加直白,网民从共同或者相似的情感经历出发,将自身从“新闻受众”转化为“情感受众”,并呈现出“反思性情感”的个体表达逻辑(田浩,2021)。在一些极化事件中,群体的情感控制却成了奢望,网络群体因为情感而聚集,不同话语结构的群体相遇时,“我们”自然区分为“我们-他们”,人们的对立情绪由此激发,导致网络空间话语转变为谩骂、相互攻讦,甚至罔顾事实,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网络审判,造成情绪性表达弥漫,同时挤占理性话语的表达空间,这不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以及和谐稳定局面的维护。当不同情感成为群际之间沟通的障碍时,情感关照就成了最好的沟通桥梁。
乔纳森·H.特纳(2009:19)认为,“情感是人类行为的调节器,需要在多种情境中保持它的运行,以使人们获得积极的体验和避免消极的体验”。哈贝马斯也肯定了共情/同情在对话中的情感价值,认为对话的参与者都必须能够换位思考,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以此构建对话团结的基础(Habermas,1990:182-202)。共情能够让人类成为一个整体,可以相互感受对方的幸福与悲伤,使得人与人之间可以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共情是儒家思想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感同身受”“将心比心”等行为的表现(郭蓓,2019)。吴飞(2019)认为,共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换位思考,来理解别人的思想和感受。共情能够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同情心理,并做出利他的行为。有研究者认为,共情的产生包含“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和“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三个阶段(Decety & Meyer,2008)。通过以上三个阶段,共情能力将“我”扩展为“我们”,有助于唤醒不同群体中个体的自然身份和社会身份。在当前各种各样的群体极化事件中,虽然算法导致用户关于世界镜像认知的“碎片化”,以至于网络充斥着各种纷繁复杂的意见,无法融合无法统一,但人们对事件的热情参与背后蕴含着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元素。通过激发起相似的情感元素,可以重新凝聚起散落在网络各处的观点和情感,实现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尊重他人在网络空间中的发言权利,让人们重新回到平等对话、杜绝对抗的公共领域,从而为由对话达成共识创造条件。

(三)“共识”:构建对话目标的实现机制
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共识不断构建的历史。17世纪中叶,英文中“共识”(consensus)一词从拉丁文中“consens agreed”和“agreement”演化出来,翻译为一致的意见,主要用来表示群体中共同认可的观点(樊浩,2014)。共识成为一个现代话题,则是伴随着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对于“共识理论”的研究兴起的。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社会共识通常被看作协调社会、促进社会和谐运行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帮助规避社会现实中的冲突与对抗,构建公共生活中的交往理性与价值秩序(赵文龙、贾洛雅,2020)。
那么如何构建社会共识?社会共识形成于平等的对话沟通之中。哈贝马斯认为,达成共识有赖于构建一个“理想的言辞说境”,对话中的每个参与者都能平等、自由地表达意见,也可以对任一参与者进行质疑。受质疑的一方可以通过反驳、说明、解释等行为借此修补或支持自己的观点。最终,较好的论据成为决定共识达成的重要因素(赵一凡,2008)。当网络沟通空间中信息共享的障碍、群体极化、群际之间对话的鸿沟被纾解的时候,我们就距离“理想的言辞说境”不远了。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3] 从现实角度来讲,我国公众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虽然当前转型社会中存在多元的利益,但是在基本的目标、基本的道路、基本的制度认定上,公众之间是存在基本共识的,这也铸就了网民之间、群体之间对话的共同基础,以此构建公众在网络对话中的底线共识,将发挥更大的社会整合效用。

(图片来自网络)
注释: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 全媒派.互联网新巴别塔:从圈子到知识分层,我们正在变得更加单向度。
[3] 新华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后。
作者 韦龙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助理研究员
版权声明
本篇文章发表于《新闻大学》2021年第10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
韦龙.重返对话: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化解路径研究[J].新闻大学,2021(10):30-4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