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娜 发布时间:2021-08-05 来源: 镜鉴工作室+收藏本文

李良荣,1946年出生,浙江宁波镇海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68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江西省吉安地委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十年。
1979年7月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新闻学者王中教授。1982年7月留校任教,1985年晋升副教授,1992年晋升教授,1986年至1992年出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在2006—2013年间,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形神矫健,谈吐睿智,风骨清奇,举止可亲,这是李良荣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位新中国著名新闻理论大家王中先生的高足,不仅深得其师真传,继续在理论新闻学的殿堂中勤勉耕耘,并且良弓无改,踵事增华,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中又一座不可绕过的高峰。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与新中国共成长的经历让这位七旬老人对起伏辗转的人生际遇常怀敬畏与感恩,他在30余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孜孜探索,直道而行,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学术佳话。
“感恩之心常给我带来满足感和歉疚感”
感恩,是李良荣回溯自己人生时最核心、最动情的词语。“我是个农家子弟,我的整个小学教育都在农村,父亲初小毕业,母亲是个文盲,兄弟姐妹六个,家境很艰苦。在家境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我能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大学教授,确实永存感恩之心。”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传统正规的教育走到今天,爱国心与责任心成为那个时代赋予李良荣并伴随他的最深烙印。“这种感恩是感觉到国家对我不薄,社会对我不薄,学校对我不薄,命运对我不薄。这种感恩之心带给我的既有一种满足感,又有一种歉疚感。我总感觉到自己做得不够,对国家、对社会、对曾经培养过我关心过我的人报答得不够。我是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我们这批人的基本素质中都有爱国情怀,有责任心,对家庭负责任,对工作负责任,对事业负责任。所以对待工作,我总是一种兢兢业业的姿态。”
感恩让李良荣时刻保持平和的心态,时刻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我这个人总体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毕竟我们是从非常传统正规的教育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但是我既传统又创新,既保守又不甘于守旧。我内心一直都有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带给我的就是,我从不妒忌别人,不妒忌任何比我有成就的人,不妒忌任何比我有地位的人,不妒忌任何比我有钱的人。我仅仅感觉到我的心态很平和,基本上没有当今社会所具有的那种焦虑感。这也是我整个人生的基本状态。”
真味无源,真水无香。李良荣对“真”字还有着独特的理解。李良荣说,“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真——做人很真实,待人很真诚。也许生活中我会说一些恭维人的话,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我绝对不会去愚弄别人,哄骗别人,更不会去装腔作势,曲意逢迎。无论是在我的课堂上还是在我的学术著作里,我在陈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时候,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一个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生的态度,无论是做学问也好,还是做任何其他事情也好,‘真’字都是我一以贯之的性格”。
正如李良荣所言,如果说感恩带给了他满足与平和,那么真实则成就了他周身的魅力。因为满足所以平和,因为平和所以不逢迎,因为不逢迎所以说真话,因为说真话所以回报他的是透彻痛快的人生。
“在我所有的头衔当中,我最看重教师头衔”
李良荣曾先后荣获复旦大学“我心中的好老师”与“我心中的好导师”称号。这意味着他在学生心目中是有口皆碑的好教师。即便如此,李良荣当上教师的心路历程却并不平坦。“我当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因为在我留校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太合适教书,比较适合当记者。”李良荣解释道,“虽然我从高中时候就开始读很多书,但大多是一些文学艺术作品,而真正学术研究的理论功底最早的时候我并不厚实。我的特点是思维非常敏捷,动笔很快,这些都是当记者的优势。我一直觉得当老师将来是要搞学术研究的,至少理论功底需要好,所以就认为自己不太适合,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当了老师”。敏捷的思维判断与倚马可待的动笔能力让曾经的李良荣对于记者这一职业的向往超过了教师,当然这其中还因为他颇为自谦的理论功底和不甚自信的普通话水平。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时代机遇让他最终还是走上了教师岗位。
“既然我当了老师,就必须尊重她的神圣性。当好老师永远是第一位,这是立足之本,做人之本”,李良荣感慨说。“后来我就开始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了,你看,当老师多好啊!虽然我教给了学生很多,但学生也带给了我很多。如果说我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学生某种知识和研究问题的思路,那么学生也给了我青春,给了我生命的青春,给了我学术的青春。学生给我带来了无穷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还要感谢这批学生。他们总是用一种求知的渴望进入作为我学生的行列,他们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总是用最前沿最新鲜的知识带给我很多启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教学相长’,尽管这话显得老,但这绝不是讨好。如果用商品交易的比喻来说,我和学生是‘买卖公平’。从这一点上,我喜欢我的学生,”李良荣笑道。李良荣不愿意把自己理解为是在教导学生,而更愿意将之视作一种与学生的平等互换和交流。他感谢学生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问题,感谢学生因求知的渴望而站在他的面前,感谢学生用不同的学科背景,用源源不断的前沿信息和新鲜观点带给他的启发和触动,而这一切对于学生的热爱都源自于他精神深处与学生平视的尊重。
谈到择才的标准,李良荣聊道,“2000年以前考博士生的还比较少,我基本上是能考进来一个是一个,能考得进来我就带。现在其实我选人也没有什么过于严格的标准或者固定的模式。但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有事业心,有责任感,这是两个最起码的标准,此外脑子比较灵敏也是我选择学生的重要指标”。而对于成才的路径,李良荣也有着深刻的经历与体会:“许多人总是会说,李老师是凭着他的聪明做学问。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我是非常勤奋刻苦的,这个你可以去问问新闻学院的门卫,因为在新闻学院待的时间最久的常常就是我。节假日里,整个大楼有时就只有我和门卫两个人。我在这里默默地做我自己的事情,看书、写文章、整理资料……任何事情如果仅仅是凭借小聪明的话,那实在是太容易了。搞学术研究,凭一点小聪明可以写一些小文章,但一定不会有大手笔,不会有非常具有创新性并且值得同行记住和借鉴的观点,因为这是需要非常刻苦才能换来的”。李良荣说,“我不否认天才,但是天才只有那么几个人。对于一般人来说,不付出艰苦努力,确实就是做不出任何成绩。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以通过这么多年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你读了多少书你就有多少功底。而悟性、灵性,只是画龙点睛的那一笔”。在苦干与巧干之间,李良荣坚持让学生以苦干打基础,以巧干求升华。他欣赏悟性所能带来的登顶的灵感,但更相信“一本书、一本书地去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探索”,才是所有人成才的必经之路。
不仅如此,李良荣对自己还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学生信任他,跟了他三年,他一定要让学生有个质的飞跃。“在我所有的头衔当中,我最看重教师头衔。我的学生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能超过我,那是我当老师的失败,是我没有教好学生。不管怎么说,学生进到我的门下,选我当导师,那是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就一定要做得像模像样,让他们感到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如果我教出来的学生完全克隆我,或者跟我差不多,那社会怎么进步,那我当老师干什么?所以我的学生,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发展,当老师也好,搞研究也好,或者从事实践工作也好,但我就是希望他们的成就要超过我。”
李良荣对学生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我认识很多非常有名的教授,他们对待学生都非常好。我对学生的所谓好,也并没有刻意地去做什么,我仅仅是觉得当老师就应该这样做,我不求学生对我的回报,我相信师生之间是以心换心的,我的学生对我也都非常好,这就是最原始的想法”,李良荣欣慰并且淡然。
说到这里,李良荣聊起了一段往事,“有一次,一个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问我,‘李老师,我们这里有一篇文章对你的观点提出质疑,你看要不要登?’我说你们该登就登,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总是觉得自己一贯正确的想法,人家对我提出不同的建议,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啊。如果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人家提出来批评,这是很好的事情。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能够和大家商量商量,也是很好的。我哪有那么霸道,好像自己一生都正确,别人都动不得,或者自己特别要脸皮,不准别人提出批评意见,一批评就暴跳如雷,对不起我不是这样的人”。
平等与开放,这是李良荣为师之道的一条法则,他不但身体力行地要求着自己,更是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学生。以诚相待,以心换心,言传身教,春风化雨,那位当年无意于从教的年轻人已然升华腾挪,师之表率。
“我的研究比较关注当前的东西”
李良荣的研究取向概括起来就是着眼当前社会,关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他认为,新闻媒体为了适应现实的需求总在不断地变化,而新闻学研究也理应针对具体问题,发挥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200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其推出的自选集上。这部自选集涵盖了他从1981年到2003年的研究精华,在从百余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32篇里,除了少数几篇涉及新闻业务之外,其余都是针对中国新闻改革的研究,并且书名也定为《新闻改革的探索》。可以说,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历程中凝聚了李良荣无怨无悔的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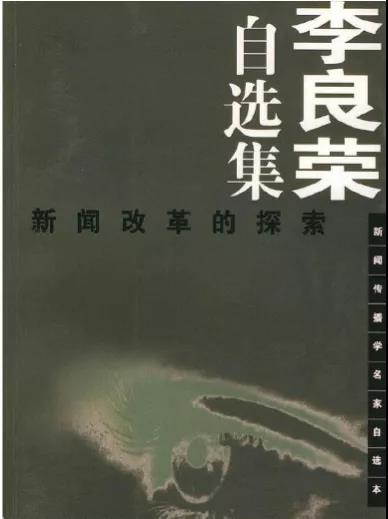
《新闻改革的探索》
在新闻改革的宏大话题之下,李良荣最为关心的是传媒的制度问题、传媒的结构问题,以及传媒的公共性问题。他说道,“我最关心、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传媒制度建设。所以凡是和我们国家的传媒制度建设相关的领域,我都关注得很紧”。他谈到,“传媒的制度问题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传媒和受众或者说与社会这三方面的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最根本的问题,包括国家的一元要求与社会的多元诉求。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制度问题主要就涉及这三者的关系。我认为到了目前,中国新闻改革不在制度上突破的话,中国新闻改革不会有出路。制度上的突破并不是说否认党的领导,或者党不要领导媒体。我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是说党要能够更好地领导媒体”。
他进一步强调,“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既需要党对媒体的领导,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这个基础在中国不能改变,同时又需要给媒体更多的自主权,让它能够成为市场的主体。也就是说不要把媒体弄得死死的,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于上面。它没有自主性了,也就不会有创造性”。他多次谈到对媒体缺乏自主性与创造性的担忧,认为一旦那样,媒体就沦为单纯的工具,而媒体人也将成为不折不扣的工匠,这是很可悲的事。因此,在媒体如何实现国家一元要求与社会多元诉求的平衡上,他一直在思考制度上的探索空间。“既不能动不动就说党管媒体多么错,这种说法不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不能把传媒业管得太死,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这就是我在研究当中的一个宏观方向。这种制度的实现是需要进行理论探索的。”
关于结构问题,李良荣对当前我国传媒格局太小、太散、太滥表示担忧。他认为,即便成立了各种规模的传媒集团,当前以行政区域划分的占山为王、各地称霸的现象,依旧使国家传媒发展的整体格局表现出碎片化的遗憾。与传媒制度一样,这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与探讨。
而谈到关于媒体公共性的问题时,李良荣不无忧虑地说,“我们的媒体不断在削弱自身的公共性,不断地在侵犯公众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媒体没有公共性,媒体没有责任心。它只对国家负责,只对自己负责,而不对我们公众负责。所以我不断地说,公众利益是媒体的立足之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公众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看上去,口头上人人都会讲都会说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公众服务是我们国家传媒业的宗旨,但是有几个媒体是真正在执行贯彻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断呼吁和强调媒体公共性的原因。这需要一整套严格的制度来规定传媒必须为公众提供那些服务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舆论监督权”。
说到这里,李良荣顿然充满了反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提出了传媒业的双重属性问题。使得媒体产业发展可以得到一种理论支撑,可以理直气壮走向市场。当时我用双重属性的办法,是想让传媒既坚持党的领导,同时能够通过企业化的办法走向市场。但这种商品性其实又丢掉了一个更基本的属性,那就是媒体的公共性”。李良荣坦言:“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现在是自己在纠正自己探讨上的失误。现在的很多媒体完全市场化了,不断地削弱公共性,不断地侵犯公众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媒体没有公共性,媒体没有责任心。它只对国家负责,只对自己负责,而不对我们公众负责”。为此,到了新世纪以后,李良荣不断地写文章强调公共利益才是媒体的立足之本,并一再呼吁抑制媒体的商品性、商业操作等问题。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2月,以李良荣为核心的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李良荣多年来对中国传媒业与国家发展问题积极关注不懈探索的学术征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研究中心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以“传播与国家治理”为方向的研究机构,整合了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7大学科团队,以建设一流的新型高校智库为使命,针对当前新传播革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构成的现实挑战,围绕传播与国家治理相关重大问题开展系列研究,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运行提供全方位的决策咨询服务。截至目前,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已为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了颇多决策咨询服务,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上海市委办公厅等机构都与该中心建立起了长期咨询关系。可以说,这位为新中国新闻改革事业殚精竭虑奔走呼号的学者正矢志不渝地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实现着紧贴时代、经世致用的学术超越。
“我不认为我是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
曾经有媒体将李良荣描述为“中国新闻学界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李良荣照单全收,而“最后一位”,他不以为然。“理想可能就是有些乌托邦式的想法,从学术研究来说,我这个人确实充满了理想,但我不认为我是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因为在我们这个学术圈里,有一批人还是很有追求的。可能由于时代的不同,大家所树立的理想标准会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不缺乏理想。我一直讲,没有理想就不要搞学术。”
理想主义,绝不是李良荣佩戴在身上的光环,而恰是他身为学者最本真的风骨和学海生涯最深刻的动力。“没有理想就不要搞学术,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为了探索一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学术就是在追求一种理想,并且提供一种实现这种理想的可行性的方案。从某种程度上讲,理论研究就是在追求一种理想。”这是李良荣反复强调的观点,“如果看看我们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30年前我们有设想到30年以后的中国会有今天?这是出乎于绝大多数人意料之外的一种成就。我们国家取得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都要比以前开放多了。30年对一个人来说,虽然是漫长的,但是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说,那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中国利用这些时间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未来30年谁又知道会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自己的理想,对未来充满乐观的原因”。
在今天的学术圈,为稻粱谋而奔命,为五斗米而折腰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少人在现实的压力面前早已不熟悉何谓学术研究的快感,这或许正是因为对理想的忘却。李良荣说:“因为有理想的支撑,我就会感觉到,每写好一篇文章就能写出自己的思想来,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做学问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很痛苦,写文章对我来说一气呵成,非常痛快”。他劝诫青年研究者:千万不要把做学问当做一种苦差事,如果你把它当做一种苦差事,那么学问肯定做不好。“即使在我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个小圈子里面,都有许多志同道合者,大家在一起可以谈得很投机很开心。我们在追求上都是一致的。如果说搞学术就是为了稻粱谋,就是为了评职称,那一定没有乐趣。正是因为有了理想的支撑,搞学术才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才会感觉到因为自己的探索能距离自己的理想又近了一步。我一直都是脚踏实地地在从事那些我认为非常值得的研究,我总说我是在追梦,梦不就是理想吗?”李良荣莞尔一笑。
“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能够称作知识分子”
李良荣曾经用江湖知识分子、广场知识分子和庙堂知识分子来形象地区分知识分子的类型。在被问及自己所属何者的时候,他笑称,“我既不属于江湖,也不属于广场,我大概属于这三者之间的混合吧。像我这样的,既关心时事,可以说有些广场知识分子的味道。我又愿意埋头做自己的学问,那么有点江湖知识分子的味道。同时,我又想为国家出谋划策,又有点庙堂知识分子的味道,所以我应该算是一个混合型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三者之间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对公众与历史的使命感以及对公众与社会的责任感。并且,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还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批判上,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能够称作为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李良荣的态度十分鲜明:“这里的批判一定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指责、一种抱怨、一种牢骚,那不是一种严肃的批判。批判是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并且勇于指出现实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批判精神。”
与理想主义的李良荣相辅相成的是,批判气质的他更显得对于理想的信仰与尊重。他说,社会与国家的任何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心怀理想,从而不满足于现状,从而思考,从而批判。“社会和国家的任何一点进步总是从不满足于现状开始的,为什么你要搞学术研究?就是因为有现实问题需要你去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些现实问题国家才能够发展。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成绩属于过去,问题属于未来’。因为现实和理想之间一定是有差距的,所以只要你有理想,那么如何去实现这种理想,就意味着一定要抓出现实当中的问题,这就体现出了我所说的批判精神。如果你觉得样样都好了,看不出任何问题所在,也就是说现实已经达到了你的理想,那你又怎么进步呢?所以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致的东西。”
在日常的教学与导学中,李良荣也不时提醒和鼓励自己的学生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积极的批判精神,并且告诫学生,知识分子的批判不等同于老百姓的牢骚。“知识分子不应该让自己停留在牢骚层面,老百姓可以发牢骚,当学者的不应该发牢骚,如果你把自己仅仅停留在发牢骚上,那么谁来研究问题呢?当学者的应该从老百姓的牢骚当中去获取灵感,知道老百姓对这个不满,所以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知识分子也是牢骚满腹,那就是混同一般的人,那你不配当学者。所以批判一定是建设性的批判,没有理想的批判就是毁灭性的批判,就是一种破坏。”
“人贵有自知之明”
从1982年留校任教至今,李良荣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工作了30余个春秋。抚今追昔回首人生心路,李良荣难忘每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人。
“在我的一生当中,在学术上给我影响最大人的是王中,他给了我学术的生命。所谓师傅领进门,是他把我领进了学术研究的大门,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他非常睿智、非常敏锐,不像别人那样死读书,在这一点上我有点像他,继承了他的一些作风,这是在学术方面。在我的人生经历上,我在小学、初中、高中时,一直都是团干部、班干部,所以跟老师的接触也比较多,那些历任的班主任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好的教育。还有我的家庭,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虽然称不上什么伟大,也谈不上什么杰出,但是他们作为最普通最平淡的中国百姓,他们所拥有的那颗对国家对社会的感恩之心也教育了我。‘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曾经的语文老师就给我讲过这句话,他说,‘李良荣啊,人这一生当中只要能做成一件事情,就很了不起了’。我一直记得他这句话,把这句话一直放在我的脑子里。所以你看我的工作简历是多么简单,我大学毕业就到江西工作,江西工作回来以后就回复旦,我这一生就两个工作单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人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不要老想着自己本事很大,样样都能做。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非常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我就会让自己不要去妄想,我这一生就是教书,搞新闻学,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跳槽出去,或者是去搞其他什么东西。教书就很了不起了,教新闻学更了不起,虽然所有的学科都瞧不起新闻学,但是我不觉得这样,我有时还会忍受别人对我的嘲弄,但我觉得只要有自知之明,我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李良荣坦言自己在复旦有一批关系很好的教授朋友,历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都有。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找了一批年轻的人文与社会学科方面的学者,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身为其中之一的李良荣就幸运地认识了这批人。在和他们的交往中,他学到了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为此,李良荣一直强调新闻学研究要多借鉴其他学科的营养,主张“功夫在诗外”的蹊径。这一点也应该与他早年从中获益良多不无关系。开阔的学科视野是打开研究思路的前提,而贴近现实生活的姿态也是做出好学问的关键。丰富的人生经历给了李良荣对党政机关运作与企业运行流程的充分了解。20世纪90年代后期频繁往来于美国的生活也使得他对于西方社会有了自己的深刻洞察与全面思考。
李良荣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一些青年学子,他们读的书可能比较多,外语也比较好,但往往就是对中国社会不熟悉,不了解党政机关的现实运作,不了解基层百姓的真实生活,不了解企业的运营过程,所以他们往往死抠书本,从概念里来到概念里去。他们因为对现实不了解,所以也不能很好地运用理论去解释现实。我觉得我的视野比别人要开阔一点,不是死抠书本。当我到媒体去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媒体希望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理论可以让他们明白这一点。我非常明白这些媒体想要获得什么,我非常明白这些媒体他们有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我所从事的这些研究,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抓的一些问题都是非常现实的,都是最前沿的,也都是令大家最苦恼的问题,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如其所言,李良荣与全国知名媒体的关系也非常好,许多社长、总编辑都愿意跟他互换意见,交流想法。在媒体老总求教于他的时候,他每每切中要害、直指锋芒,令人叹服。
人贵有自知,而自知正是因为内心的丰富与饱满,是直面人生的大谦卑与正视自我的大自信,是云淡风轻,是不卑不亢,是不妄言不虚饰,是踏踏实实地行走于人间正道,是用得起无悔无愧来描述自己的人生。“真金不需镀,静水自流深。”古人以此来形容有真才实学的人用不着无谓的装饰,来比喻内心淡定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其实,这也是对李良荣的真实写照:有知恩图报的责任担当,有循循善诱的师道风范,有信仰理想、勤谨务实的学术追求,也有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的至情至性。
“我没有文章是见风使舵的,只按照自己的目标,按照自己的理想在走。所以我写的文章没有什么是追悔莫及的。”回首几十年的学术人生,李良荣坦荡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