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良荣 发布时间:2024-02-25 来源:澎湃新闻+收藏本文

文 | 李良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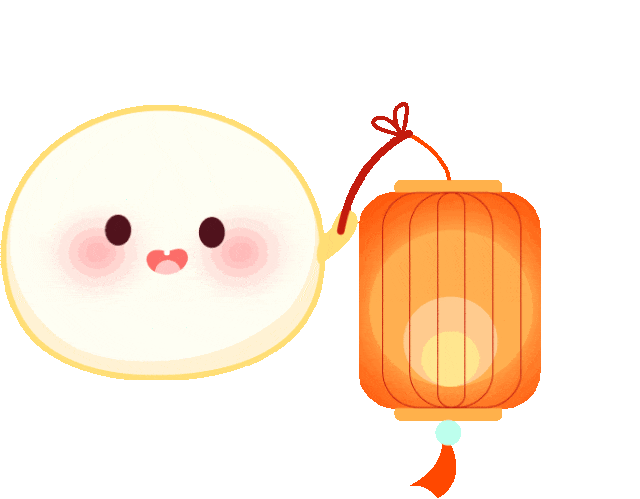
2024年元宵节将临,电视上照例播出各地尤其农村地区准备红红火火闹元宵。今年是龙年,多姿多态的舞龙节目成了元宵节的重头戏。过了近80年的元宵节,我看过几次舞龙表演,但从未加入舞龙队伍,却参加过两条“龙”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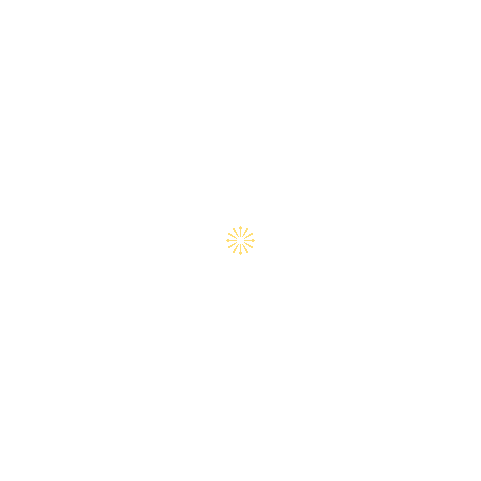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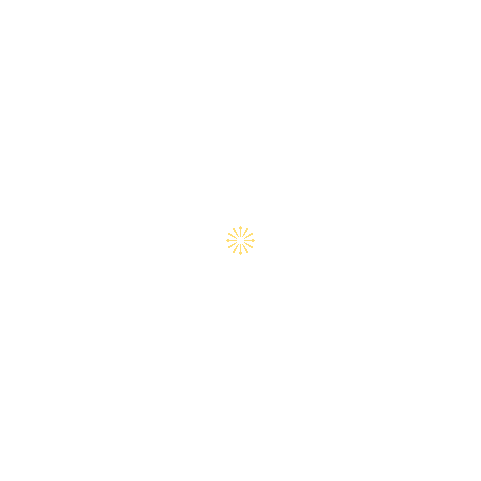
1956年元宵,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在家乡小山村(宁波市柴桥镇东山门村)度过。
那年,临近元宵,小山村依旧冷冷清清。我那时才十来岁,也不明白元宵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元宵节小孩可以放炮仗。我当时的唯一奢望是有五分钱买一串小炮仗放放,但也没敢向母亲开口,五分钱在小山村就是一笔大钱了。元宵节前一天,我母亲炒了一盆黄豆,这难得的美味已让我们欢天喜地。晚上,一盏煤油灯下,我们兄弟姐妹围坐在一起,嚼着黄豆,我母亲做着针线活,给我们讲起当姑娘时度过的元宵节。母亲生于1922年,当姑娘时应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我母亲识字不多,但讲起当年过元宵的场景却绘声绘色,脸上不时绽放难得一见的笑容。
“那些年过元宵,柴桥街上真热闹。”这是母亲描述元宵节的开头语。柴桥是离我家七八公里路的集镇,当年号称“小宁波”。随着我母亲娓娓道来,柴桥镇上元宵节热闹的场景便一幕幕展开。
柴桥镇上闹元宵,开场是舞龙,龙头到龙尾有一百来米长,龙头左右摇摆,龙头前小狮子前后翻腾,引得满街喝彩。紧接着是踩高跷队伍。每一座高跷都装扮成各色各样的历史人物,我母亲能数得出来的有白娘子和法海、梁山伯和祝英台、唐僧和孙悟空、白无常和黑无常。梁山伯和祝英台边走边唱《十八相送》。我母亲说:“扮孙悟空的本事最大,一边踩高跷,一边手舞金箍棒,一大帮小孩子跟在他后面。”再后就是附近各村的表演。“大家都想别苗头,一村要比一村好。”我母亲特别兴奋:“当年我们钟家堍特别出风头。”钟家堍是我母亲的娘家,是柴桥镇下的大村。村子里找了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扮成散财童子,敲锣打鼓,吹吹打打,一面向两边观众撒熟花生,当地人称“撒金豆”,抢到越多,福气越旺。小孩子都追着跑,街头一片喧闹。“闹元宵,真正好热闹。”我母亲最后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
母亲讲的闹元宵故事滋润了小山村冬夜的干枯,令我神往,充满渴望,幻想着再来一次闹元宵,自己也能扮一回散财童子。于是,我傻傻地问:“那现在为什么不办了呢?”
我母亲叹口气,摇摇头,没回答我。后来,我读到辛弃疾的词《青玉案·元夕》,我老家当年闹元宵活现了辛弃疾笔下的场景,我甚至想象当年我母亲的发髻上是否也插着“蛾儿雪柳黄金缕”,人群中那么出彩。但“现在为什么不办了”的疑问一直困惑着我的少年时期。
元宵节那天,吃过早饭,我无聊地站在村口,一片薄雾在小山村飘荡。我幻想着有支舞龙队伍突然从山间小道上冲出来,但只有几只乌鸦“呀呀”鸣叫着,掠过低空,小山村还像以往那么寂静。乌鸦的叫声在我们当地农村视为不吉利,我用“呸呸呸”来回击乌鸦,实则是想吐掉心中的郁闷。
眼看着元宵节只能在想象中度过,母亲却给了我们天大的惊喜。那天下午,母亲用长长的竹竿扎了两把竹篓子,吃过晚饭,把竹竿交给我们,说:“过会,隔壁赖家阿叔带你们去烧田龙。”这真是喜从天降啊。我们小山村二三十户人家只有两个姓,一个姓李,一个姓赖,赖姓是外来户,听说是好几代以前从苏北逃难过来的。两姓村民相处很融洽,赖家阿叔我们都叫他赖叔,当年也只有20来岁,没结婚,童心未泯,偶尔还会领着我们几个小屁孩儿下河捕鱼捉虾,小孩子都喜欢他。
所谓烧田龙,就是烧田垄,放火把各块田之间田埂上的茅草烧掉。1955年春节后,我们全家刚从上海回到老家,元宵节那天,看到过小孩们烧田垄,但母亲怕有危险,不让我们去,只能站在村头看别人玩,心里满是憋屈。这次总算如愿了!
到晚上七点钟左右,赖叔把我们七八个小孩集合在村口。那天晚上,天气实在遂人心愿,皓月当空,晴空如洗,笼罩大地,大地一片银装,一片静谧。地面上飘着微风,流经小村的芦河泛着粼粼银光,静静流淌。赖叔向我们宣布纪律:我们烧的田埂从村头到小石桥大概有四十来条,小石桥外归其他村子。他特别叮嘱:一定小心不让火苗蹿到衣服上。
赖叔一说完,我们这群小屁孩儿就呼喊着,像冲锋的战士扑向各条田埂。我们每人手上一把长杆竹篓,我母亲想得周到,竹篓里裹上干茅草,赖叔拿出火柴,一点就着。我们从田埂头上点火,田埂上主要是茅草,还有些小芦苇、蓬蒿、硬秆类的植物,经过一秋一冬的暴晒,已经很干燥,一点火,茅草呼啦啦就烧起来了。火势顺着田埂,慢慢向前爬行,时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炸裂声,火苗四射,甚至蹿上几丈高。我们还把田埂旁的两块茭白田也点燃了,那火势更猛,烈焰滚滚,像只大火塘。当我们把四十来条田埂都点着,邻村的孩子也都点燃了田埂,一时火光四起,把天空都烧红了。赖叔赶紧把我们叫拢在一起,站在小石桥桥头上环顾四周。远远近近,条条田埂都在燃烧,像一条条火龙爬行,时不时响起“噼噼啪啪”的炸裂声,整个田野笼罩在火光烟雾之中,充满着焦香味,我这才体会到烧田垄为什么叫烧田龙。我们站在桥头,跳啊喊啊,尽情宣泄着内心的兴奋。估摸着两个小时,火势才慢慢熄灭。因为田里都种着绿肥红花草,不会发生火灾,赖叔领着我们回家。
路上,我问赖叔:“为什么元宵要烧田垄?”
“杀虫啊!”赖叔回答我:“到了冬天,天冷了,病虫都钻进田埂里,烧田垄就可以杀死它们,草灰还可以当肥料。”
于是,我们一路蹦一路喊:“烧田龙,杀害虫!”
到了村口,赖叔问大家:“开心吗?”
我们都齐声回答:“开心,穷开心(当地方言“穷”为副词,“非常”的意思)!”
穷开心,穷且开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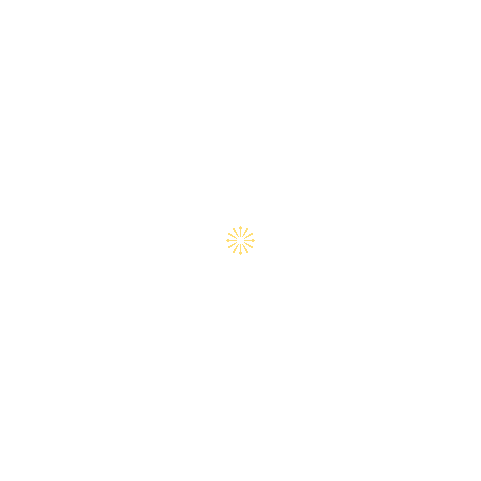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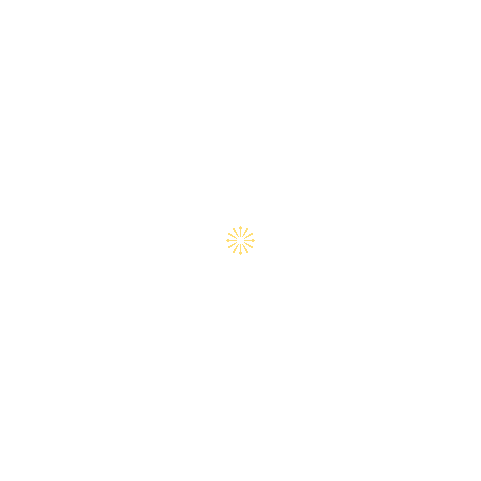
1970年元宵节,我在江西省峡江县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度过。
1969年12月底,我大学毕业经过一年劳动锻炼后被分配到江西省吉安地委(当时还称革委会)宣传部工作。1970年元宵节前一天,部里派我跟宣传部一名老同志赖昌材去峡江县调研,调研内容是没有回家过年的上海插队知青状况,以及知青回乡的准备工作。这是我入职后第一次出差,尽管马上过元宵节了,但也不能不去,好在老赖是资深的农村工作者,为人极厚道。我入职后,他不时指点我,待我如兄长,所以,我也很乐意陪他去。我们按县、公社、生产队三级调研要求,在县、公社了解知青面上情况后,元宵节那天,我俩到一个小山村去了解点上情况,我们选了靠近峡江县域不远的水背村(具体村名记不清了,这是从当地地图上查出的村名,可能有误),那里有6名上海知青。
我们从镇上出发,沿着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一路爬山,两个来小时,翻过一座小山头,一泓湖水突现眼前。湖水碧绿,山风吹过,湖面波光粼粼,映衬在湖面上的白云在波光间漂浮,远山苍苍,近山树木茂盛,鸟鸣婉转,好一幅湖光山色图,让我们心旷神怡。我们知道,水背村快到了,因为公社文书告诉我们,水背村原先散落在一条狭长的峡谷里,村子里三十来户人家,多数姓姚,十几年前修了水库,村子全淹没了,但村民不想外迁,在山腰上建了一个新的水背村。
果然,我们下山没多久,一名50来岁的老农迎上来,满面笑容,自我介绍姓姚,是生产队队长,我们称他姚队长。姚队长一把抢过我们的行李,领着我们进村,路上告诉我们:“我们村又偏又小,新村建了十几年,公社干部只来过几回,县里干部没见过,今天元宵,迎来地区大干部,我们村的稀客。”这话倒体现山里人的实诚。姚队长把我们领进客房,房间里一张大床,两条新被,整整齐齐,看来刚刚打扫过。姚队长还连声道歉:“这是我弟弟家的房,几小时前才接到公社通知,临时安排,条件不好,比不上你们城里。”刚刚放下行李,一位中年婶子提着热水瓶,一脚跨进来,扯开嗓子就大呼小叫:“今天我们家好福气,双喜临门,新姑爷上门,地区又来大干部。”一边给我们沏上茶,“晚上,让新姑爷陪领导喝几杯。”姚队长介绍:“这是我的弟媳,山里人讲话嗓门大,别见怪。”“新姑爷”一词对我还挺新鲜,等他们走了,我问老赖:“新姑爷是什么人?”老赖是本地人,回答我:“新姑爷就是女儿的未婚夫,第一次上门来拜见丈人丈母,女儿家肯定要热情招待的。”噢,原来就是上海人称作的“毛脚女婿”。
休息一会,已是下午三点多钟,姚队长来领我们去村里走走。水背村朝南,面临水库,背靠大山,村子沿着水库一字形排开,房子看上去还很新,收拾得很干净。姚队长站在水库边介绍说:“水库里年产十来万斤鱼。库边有五六十亩水稻田,水上新辟百来亩山地种杂粮,种了很多油菜树。” 听上去很富足。在村中的空旷处,已堆了不少柴枝,姚队长说:“今天元宵,全村人聚在一起烧篝火,热闹热闹。这些年,年年都这样过。”最后到知青住房,六名上海知青,四男二女,都回上海过年去了。三间住房,屋子没锁,我们进去查看,收拾得很整洁。姚队长说,六名知青在这里很受村民欢迎。过去村里小孩翻山越岭去上学,很难,现在这里设一个小学的教学点,二十多名孩子,六名知青轮流给他们上课,晚上还给孩子们讲故事。两名女知青曾去县里培训过,当上赤脚医生,村民小病可以不出村。
回到住宿处,姚队长没让我们进住房,领到了他弟弟家的厅堂。厅堂里已有四五个人围着桌子坐着,见我们进来,纷纷起座迎接我们。姚队长把我俩安排在上座。桌面已摆上满满一桌子的各种糕点:炸的、煎的、蒸的;黄的、白的、绿的,中间一个筐里高高堆起金黄色的油炸品,像盛开的大号喇叭花。姚队长拿起一颗让我尝尝,我咬一口,又脆又香。姚队长问我:“猜猜,这是什么?”我猜不出,如实回答:“从来没吃过。”“哈哈”,姚队长有些得意了,“乡下土产,南瓜花。夏天采下来,晾干,现在拿出来,蘸上面粉,油炸。”南瓜花居然能做出如此美味,让我大开眼界,禁不住吃了好几颗。当时肚子也饿了,各种糕点着实吃了不少。我以为这就是我们的晚餐,吃饱了回房休息,准备晚上参加篝火活动。谁知,一个多小时后,姚队长又来请我们去吃晚饭。到厅堂一看,桌面上堆满了各色菜肴,每一盆都堆得小山似的。一名小伙子迎上来,姚队长介绍才知是刚到不久的新姑爷,一身新衣服,个子不高却很精干。新姑爷开口说话,不像本地人,听他介绍才知是浙江建德一带人。新安江建水库,他们一村子的人都迁移到峡江县来了。我一说我是浙江人,他就陪在我身边坐下,分外亲热。刚坐定,姚队长马上给我们倒上一碗酒,举起自己的酒碗,高声说:“今天元宵,欢迎地委来的贵客!欢迎新姑爷!”一饮而尽。我喝了一口,酒暖暖的,甜甜的,有股清香,估计是他们自酿的米酒。然后,姚队长给我一大块烟熏肉,我一口咬下去,满嘴肉汁,入口即化,真的好香。我第一次品尝烟熏肉,真稀罕人间有如此美食。过一会,姚队长又撕下两只鸡腿,塞到我和老赖碗里,刚吃完,又一大块红肉,姚队长说:“野兔肉,今天上午刚打的,很新鲜。山上野兔太多了,不打也不好。”这几大块肉把我又塞得饱饱的。吃了近一个小时,老赖举起酒碗,给各位敬酒,表达谢意,然后拉着我起身告退。我不明其里,回房间问老赖为什么早早告退?老赖告诉我:“这是这一带风俗,新姑爷上门,必须让他喝够喝醉,否则整个村子没面子,说老丈人家酒不好。我们在,他们不方便。”老赖知趣而退,让我长见识了。
到晚上九点,姚队长请我们去参加篝火晚会。村子小广场上篝火烧得正旺。可能烧的柴木里有松枝,一股浓浓的松油香,随着“咔嚓咔嚓”的炸裂声,火苗四射,犹如烟花。广场上男女老少围着篝火,说啊,笑啊,小孩子满场子乱窜。姚队长在我俩面前放一张小桌,摆上藤条筐,筐里放着西瓜子、花生、炒薯片,两杯茶。这倒并非我们特殊,一家一户面前几乎都有这么一只筐。只是独不见新姑爷,姚队长笑笑说:“新姑爷喝好了。”我知道新姑爷醉了。置身于眼前热闹又祥和的乡村,远处,月上中天,伴着彩云,缓缓飘动;近边,噼啪的篝火映照着一张张欢乐的笑脸,大自然的深远神圣,人间的热闹烟火竟那么融洽地交汇在一起,我心醉了。
临近午夜十二点,一串长长的爆竹用竹竿挑起来。到十二点整,爆竹点燃,八枚炮仗腾空而起,发出震天巨响,又从群山中传来阵阵回响,村民们爆发一片欢呼。待到爆竹声停下,元宵节高潮到了。村民们人人举起一支火把,姚队长也给我和老赖各人一把干燥的硬柴枝。我俩加入村民队伍,顺着水库,排成长长一列,每人相隔一米左右。大家举着火把,在空中一圈一圈舞动着,看上去宛如一条上下翻腾的火龙,“舞山龙”的名称何等生动、形象!听着姚队长高喊:“敬天!敬地!敬祖宗!”,全村人跟着齐喊“敬天!敬地!敬祖宗!”,山谷里回荡着他们的一声声呼喊,如雷如鼓,天在呼应,地在呼应,山在呼应,天、地、人在互相呼应。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老赖原路返回。走到那个小山头,回望水背村,依旧湖光山色,一片宁静,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用惯用的学生腔感慨了一句:“像在桃花源里,悠然自在。”谁知老赖说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好在水背村又偏又小,政府懒得去管他们。没有了官员指手画脚,他们才能因地制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民怎么种田、怎么过日子,哪需要政府来教?”老赖不愧资深的农村工作干部,我越到后来越体会这段平平常常的话所蕴含的深刻思想。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官不扰民民自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