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发布时间:2021-05-03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收藏本文
★
摘要
★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5日,世界知名出版集团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首席执行官马赛厄斯·多夫纳(Mathias Döpfner)与美国前国务卿和外交官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进行了深度对谈。本文重点对基辛格就中国崛起和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洞见进行编译,以飨读者。本文略有删减,获取英文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应对中国:阻止崛起还是开放共存?
Q
据预测,2028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在拜登就任前夕,中方与欧盟全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被华盛顿认定是一种“挑衅”行为。未来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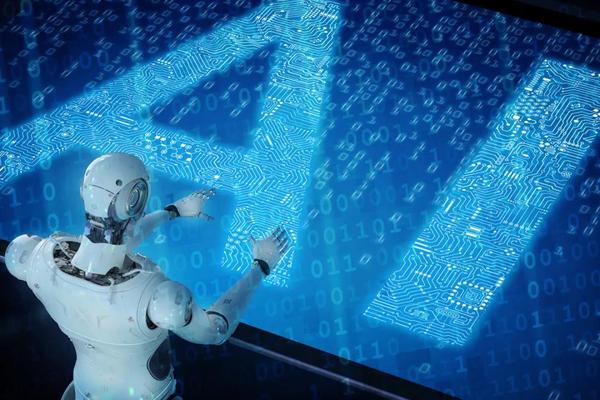
Q
提到人工智能,您认为AI技术能够对我们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新的战略手段和战争形式将不再是武器,根本上说是数据。在这方面,有些声音认为中国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的可能性不小。你是否担心未来最终可能会出现由中国单边主导的人工智能治理?
Q
美国和欧洲在中国问题上的战略分歧会对跨大西洋关系构成真正的威胁吗?
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前景
Q
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欧洲的应对近乎功能失调。有意思的是,拜登政府上任后采取了比特朗普更加严格的旅行限制。这将对重建美欧跨大西洋战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如果美欧不能重建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欧洲最终将成为亚洲的一员。您认为当下是否存在出现这种危险情况的可能性?(美国)会在重建跨大西洋关系的问题上栽跟头吗?

Q
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奥巴马上任时正是美国太平洋时代拉开序幕的时候?
基辛格:是的。二战结束不久,(美欧)有一个共同的主线,也有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重建欧洲,重新定义美国对其外交政策的态度。这是重要的国家努力。即使在尼克松时期,当人们试图重新定义美欧的正式关系时,在战略领域也相对容易操作,然而事实证明要制定一份具有政治目标的《大西洋宪章》却绝非易事。双方没有敌意,但欧洲也不愿定义一种有机的关系。现在,这一问题将由于全球性挑战再次浮现。欧洲不存在地方性的身份认同危机,所以在定义我们的全球角色时,可以预见的是欧洲会倾向于奉行一种与美国不同的政策。
在短期内,我可以看到双方都有很多好处;从长远来看,我担心的是,双方对自身利益的强调将起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它将使欧洲沦为欧亚大陆的附属物。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将专注于亚洲和近东国家之间互相竞争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努力可能会让欧洲筋疲力尽。第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将在战略上成为太平洋和大西洋交汇的一个岛屿。这样美国将采取典型的岛屿国家对大陆区域的外交政策,即以弱者对抗强者,这意味着美国将更多地关注分歧,而不是建设世界。即使美欧间能够友好地处理分歧,美国和欧洲也不应该在如何界定共同目标的斗争中耗尽精力。我们不必就每一个局部问题的每一项经济政策达成一致,但我们应该对我们希望大西洋地区在历史和战略上的发展走向有一个共同的概念。
Q
欧洲将与怎样的美国打交道?您是如何看待现任拜登政府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观念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