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逸 发布时间:2020-06-29 来源: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收藏本文
*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此前曾经引发热议的美剧《纸牌屋》,描述了雄心勃勃的下木参议员在美国核心决策圈努力攀升并最终问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曲折故事;人们在赞叹剧本作者的脑洞之余,其实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预期,在现实世界中真的看到这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毕竟人们对于政治过程,尤其是美国核心决策圈的政治过程,还是充满了某种信心或者说是某种信念的。
不过自从2016年特朗普异军突起入主白宫之后,华盛顿决策圈的戏剧性发展就持续进入某种颠覆性发展的阶段,而进入2020年之后,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这种颠覆性发展更是呈现某种密集的高潮阶段,曾经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超级鹰派博尔顿最近出版回忆录性质的《事发之屋》就成为了一个最新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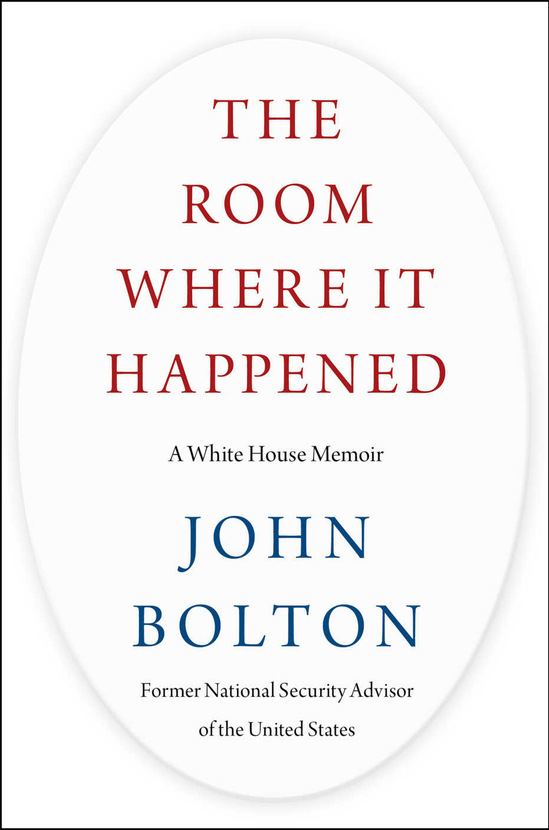
博尔顿新书封面。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高度政治性的敏感职务

从实践来看,有关美国研究的成果均显示,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大致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成为华盛顿决策圈内低调的幕后策划者;另一种情况,则是成为总统的超级代表。
需要说明的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特殊敏感职务,是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相关议题领域的主要幕僚。这个职务从1953年开始设立,隶属总统办公室,任命无需提交参议院批准。
严格来说,和国防部长等内阁职位不同,出任这个职务至少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首先,当然是在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资深经历;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当然是得到总统的充分信任。从实践来看,有关美国研究的成果均显示,大致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成为华盛顿决策圈内低调的幕后策划者;另一种情况,则是成为总统的超级代表。虽然没有正式官职,但在很多场合可以事实上超越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在美国的外交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从1953年至2020年6月,美国已经有过28任正式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2任代理。历史上出任该职务的,包括麦克乔治·邦迪(1961-1966)、沃尔特·罗斯托(1966-1969)、基辛格(1969-1971)、斯考特罗夫特(1975-1977,1989-1993)、布热津斯基(1977-1981)、卡卢奇(1986-1987)、科林·鲍威尔(1987-1989)、安东尼·雷克(1993-1997)、赖斯(2001-2005),客观上都可以看作是国家安全议题领域的一时之选,做出的贡献,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也颇为可观。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超级顾问基辛格博士。

1971年,时任尼克松总统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图片来源:新华网。
但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整个画风就开始出现了变化:首先,是走马灯的一样的换人,从2017年1月开始,已经经历了弗林(2017.1-2)、凯洛格(代理,2017.2.13-2.20)、麦克马斯特(2017.2-2018.4)、博尔顿(2018.4-2019.9)、库珀曼(代理,2019.0.10-9.18)、奥布莱恩(2019.9.18-至今)。而博尔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则成为了第一个离任后公开著述批判其服务对象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
2020年又恰逢美国总统选举年,博尔顿这时候出来批判现任总统,且大量材料据称直接源自其身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亲身经历,毫无疑问成为了极具爆炸性的新闻。《事发之屋》出版的消息刚披露,就颇有洛阳纸贵之势,本届美国政府为了阻止该书出版不惜诉诸法院但未果,则又极大的增强了各方的好奇心。
离职原因:
博尔顿个人预期与系统决策架构冲突

根据美国的制度设计,不要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种顾问性质的岗位,即使是像国务卿、国防部长这样的职务,本质上也是一个提供决策方案的建议者,真正的最终的决策者,只有美国总统一个人。
这本超过500页的英文书虽然没有什么艰涩的理论,但要啃下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与博尔顿本人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作为一名华盛顿决策圈内的公认鹰派,博尔顿1948年11月20日出生在美国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在耶鲁大学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1974年开始律师生涯,1979年开始进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当顾问;1985-1989年,在里根政府担任助理司法部长;1989-1993年,在老布什政府任内担任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1-2005年,在小布什政府任内出任主管军控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2005年后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这个代表的任命是小布什总统在国会休会期间用行政命令方式任命的,国会进入新的会期后,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坚决不同意这项任命,所以在一年后,博尔顿也就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
从这番经历来看,博尔顿确实不能说是一个资浅的人士,而且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他已经加入其中发挥了他认为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很自然的,当2016年特朗普赢得选举并开始组建自己的执政团队时,博尔顿在得知自己进入了考虑名单之后,对自己的职务是有预期的:既然在小布什政府任内已经出任过副国务卿这个职务了,那么显然,再上层楼,弄个国务卿的位置,似乎也不算什么非分之想。而且离开小布什政府之后,博尔顿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种场合和媒介上批判奥巴马政府的各种“软弱”和“不足”;当然,博尔顿很自然的忘记了自己此前的职场表现,其实已经在华盛顿的圈子里留下了过于鹰派、以至于不适合出任外交相关职务的某种印象,所以,当特朗普政府没有第一时间选择他出任国务卿,而且还是在弗林和麦克马斯特两个人先后离职之后,才最后任命博尔顿当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时,博尔顿感到的并不是什么喜悦,而是某种微妙的不满。

博尔顿。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很自然的,这种不满在《事发之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该书的第一章,名为“通向白宫的长征”,因为美国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位于白宫西翼的东南角,所以英文中直接用了“to a west wing corner office”。而从第一章的第二自然段开始,博尔顿就开始非常直接的宣泄对其曾经服务过的特朗普团队的不满,将其称之为无法用常理描述的团队;并很鲜明的形成了一个对比组:特朗普和他信任的核心团队,是一群“从来不阅读政府操作手册”(的家伙),并导致整个办公室处于“霍布斯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当然就是博尔顿自己,因为博尔顿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经验。
有了对比之后,博尔顿就产生了第二个更加微妙的想法,用他在回忆录上的说法来说,就是“不是要获得俱乐部的会员卡,而是要拿到驾驶证”,换言之,博尔顿不仅满足于进入白宫决策屋,去提供建议;而且还希望能够发挥更加实质性的作用,甚至是决策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乃至整个行政系统的决策架构,产生了冲突:根据美国的制度设计,不要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种顾问性质的岗位,即使是像国务卿、国防部长这样的职务,本质上也是一个提供决策方案的建议者,真正的最终的决策者,只有美国总统一个人。
有趣的是,博尔顿也好,此前被戏称为黑衣总统的班农也好,都多少有这种欲望,而特朗普本人,在掌握最终核心决策权上的认知,更是清晰的无以复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事发之屋》的第一章不经意间就透露了博尔顿离开白宫的核心原因:他过于强势的尝试去影响特朗普,乃至试图实质性的获取在国家安全相关事务上的决策权,而这触及了特朗普的“红线”;同时,这也有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特朗普政府很多“非常规”决策背后的真实原因:并非特朗普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战略安排或者构想,纯粹就是没有能够实现有效的整合,核心决策圈内各方人马基本处于某种碎片化争斗的状态,而这种争斗,或许在天下太平时并无伤大雅,但在遇到某些特殊的事件时,就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且美国自身必然无法置身事外。
博尔顿不仅有这样微妙的想法,而且还确实努力付诸行动,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表现在美国联合加拿大,以某种“政治绑架”的方式,形式合法但实质非法的扣留华为孟女士。这个涉及重大国家安全议题的决策,根据博尔顿自己的描述,“根据对特朗普处理埃尔多安方式的观察,我决定将所有(逮捕Meng Wanzhou的)事实都掌握到手里之后再向特朗普汇报。”换言之,相关行动是在执行完成之后,才提交到特朗普这里的,而博尔顿本人,则保持了对事态的实时关注。这理解起来并不复杂,英国连续剧《是大臣》(Yes Minister)里,这就是架空大臣,仅让其获得被筛选后的信息的标准做法。考虑到博尔顿所处的位置,所以,除非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绕开博尔顿,直接向特朗普进行情况简报,否则说博尔顿在这一问题上成功的说法,至少是有限度的架空了特朗普,是一种有可能成立的判断。
中美关系定位:白宫内部的混沌状态

特朗普真正关心的问题始终聚焦于个人的政治利益,赢得大选成功连任,很多时候成为支配其最终决策的核心动力机制。在特朗普眼中,华为更多的是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而不愿意接受班农、博尔顿等鹰派的核心观点,即华为先进的5G系统对全球安全造成的重大威胁。
就有关中国的内容来说,《事发之屋》的最大价值,在于向人们展示了白宫内部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当然是通过博尔顿的眼睛:财政部长是博尔顿眼中的亲中派;库德洛关心的是自由贸易;纳瓦罗、莱特希泽、罗斯则是鹰派三人组;特朗普真正关心的问题始终聚焦于个人的政治利益,赢得大选成功连任,很多时候成为支配其最终决策的核心动力机制。比如博尔顿描述了2019年6月18日,特朗普在G20会议前与中方领导人进行了通话,特朗普提起了2020年的美国选举,暗示中国的经济能力能够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并恳求中方能确保自己获取胜利,如果确实属实,特朗普的行为也堪称坦率到了惊人的程度。
又如,博尔顿描述称,中美贸易谈判进入尾声时,特朗普曾经提议不对剩下的3500亿美国的货物加征关税,条件是中国需要尽可能多地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此后谈判进展缓慢,导致特朗普决定进行下一轮制裁,这一决定当时引起了特朗普幕僚团队的普遍反对;以及在特朗普眼中,华为更多的是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而不愿意接受班农、博尔顿等鹰派的核心观点,即“华为先进的5G系统对全球安全造成的重大威胁。”
除了贸易问题,在更加广义的中美关系的议题领域,如美国长期关注的港台议题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所谓人权问题上,博尔顿眼中的特朗普,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地产商人,而非美国总统;被欧美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的桥段是,关于台湾问题,博尔顿在文中明确指出,特朗普深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实力悬殊,他对台湾尤其不以为然。特朗普用手指指向他常用钢笔的笔尖,称“这是台湾”,又再指向白宫椭圆办公室中历史悠久的,供历任美国总统使用的办公桌,即所谓“坚毅桌”,称“这是中国”。博尔顿对此的评价是,在特朗普这里,“美国对民主盟友的承诺和义务,不过如此。”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可以很清晰的发现,与特朗普死磕,是博尔顿出版这本回忆录的重要原因。从行文来看,博尔顿很显然的不赞同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即使拿不出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博尔顿也很清楚的发现,与之前预期的不同,因为不愿意将决策权真的交给类似博尔顿这种极端鹰派,而坚持从自身的政治利益考量来实施各种决策的特朗普,已经不太符合他们当初将其作为政治象征的预期。这无疑是非常值得仔细思考和深入玩味的。
坦率的说,无论是班农、博尔顿先后离开白宫的命运,还是博尔顿回忆录中披露的内容,让人们可以用一种更加谨慎乐观的情绪去看待和认识中美关系。今日美国核心决策团队的真实态势,已经发生了某种堪称戏剧性的转变。对中美战略博弈来说,敢于看到和承认美国真实的决策模式,避免因为“自己吓唬自己”而失去应该把握的机遇窗口,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除此之外,博尔顿的新书,用一种比较具有戏剧化的形式向我们预示了中美关系必然要面临的新型威胁和挑战:当中美两国之间的整体实力更加接近时,美国的核心决策机构更可能表现出的,是某种结构性的混乱甚至是混沌状态;美国行为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更大概率出现的事情。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有效的管控,将由内部政治因素带来的扰动降到最低,如何有效的区别美国的话语和行动,并构建与这种新态势相适应的中美关系新战略框架,更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