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发布时间:2020-11-25 来源: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收藏本文
导读
11月21日,第六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聚焦“媒介变迁与传播革命”议题,邀请8位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思想最为活跃的互联网研究学者,分享其对互联网研究的最新智慧。我们相信,新闻传播学界顶尖学者的互联网研究洞见,必将深刻形塑社会科学学科的新面貌以及未来媒体发展新方向。
“互联网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技术的变革正在使人类文明经历一场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复旦大学孙玮教授在11月21日举办的第六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上发言时如是说。
如何看待由于媒介变迁引发的传播格局、社会治理和人类的存在状态的改变?新闻传播学对这一深刻改变是如何理解的?11月21日,复旦大学第六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陈昌凤、刘海龙、胡翼青、喻国明、黄旦、孙玮、张志安、李良荣等8位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最活跃的学者,围绕“媒介变迁与传播革命”,从不同视角对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情况、引发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发表了深入的主旨演讲。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主持会议。

发布会现场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关注数据技术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她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人工智能特点是:以模仿专家的知识和人类的逻辑推理习惯为主,算法相对透明,因此,它是人类可理解、可控的一种人工智能。第二阶段的人工智能特点是:通过神经深度学习技术模仿人类的感知系统,因此,它的算法是一个黑箱,人类通常无法理解,也不知道它的运算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当这种人工智能被用在社会治理中时,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一方面,新的人工智能算法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社会治理手段,在犯罪预测、疫情扩散模拟、政治预测等方面,第二代人工智能都有较为出色的表现。另一方面,算法用作社会治理也会带来一些新问题,由于第二代人工智能算法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集进行机器学习才能生成,在这个过程中,训练数据集中包含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人类负面的东西也会被带入算法,这会使得出的算法也会包含一定的价值偏差。
同时,第二代人工智能算法催生了个性化信息生产,这种个性化信息生产目前国内的传统媒体还没有,但在国际媒体中非常普遍。在这种个性化信息的影响下,我们越来越个体化,但社会治理需要把一个社区看作一个整体来治理,因此,这种个体化跟社会治理是矛盾的。基于上述观点,陈昌凤教授提出,不论是将算法用在信息传播,还是用在社会治理上,我们都要特别重视它的科学性,需要去理解和打开算法的黑箱。因此,她建议同学们多学一些相关技术,以便随时应对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带来的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探讨了传播研究中的“身体概念”。他发现在传播学研究中,身体一直是属于“缺席的在场”。传播学研究受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影响,一直认为传播是心的交流,身体感知是不可靠的,理性才可靠。由于媒介的透明性,在日常交流中,我们也不会注意到身体的在场,但VR、AI等技术消解身体的重要性时,身体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传统研究中的身体概念有两种,一个是作为符号和象征系统的身体,一个是作为文化和权力的展开与配置的场所(place)的身体。同时,身体的概念在这些理论中是模糊的,我们在研究中通常使用的“具身”这一概念也有不同的含义。
刘海龙认为,传播研究中对身体的研究有三个传统进路和三个新进路。三个传统进路分别是:作为象征符号的身体、作为权力表征的身体、作为劳动力的身体,三个新进路分别是:作为经验感官的身体、作为隐喻及投射的身体、作为物质的身体。上述研究要么侧重于身体的物质性,要么侧重于身体的知觉及意义性,但从传播的视角理解身体时,应同时注意到它的物质性和知觉意义性。刘海龙提出,如果用身体视角重估经典传播理论,就会发现经典传播理论可以被分为离身性传播研究和具身性传播研究两类。两种研究的分歧在于:第一,什么是传播研究,是效果还是交往行为,第二,什么是媒介,媒介是工具还是具身性感知。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分享了媒介“可供性”理论的起点、理论旅行以及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呈现的可供性。胡翼青认为可供性理论充满着矛盾张力。一方面,可供性内在于环境,以环境属性作为物质基础,不会根据动物的需求而改变;另一方面,可供性必须在动物的感知、实践、行动中才能显现。这种矛盾张力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事物的不同视角。可供性理论自1979 年经吉布森提出后,在设计心理学、现代认知科学、科学社会学得到广泛应用,学者们并非将“可供性”简单理解为环境提供的客观因素,而是加入了人是怎样感知可供性这样的主体性视角。在传播学领域,广泛存在着对可供性概念的功能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完全解构了可供性概念对传播学的意义。
可供性理论并不是主客体二元割裂的理论,而是在二元基础上一元构造,主客体是密切互动、互相建构的。在可供性理论中,介质、物质和界面等概念非常重要,值得我们重视:当下传播学领域存在着诸多将“介质”变成“物质”的现象,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反思。今天,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正在合流;媒介可供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行动者视角,这是一个可自由构造的理论框架,富有细节张力;关于对外传播、媒体融合等研究主题,我们都可以从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在本土实践中建构具有本土化意义的传播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喻国明教授围绕《未来传播研究的三个可能性关键》发表了主旨演讲。喻国明认为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社会“媒介化”:媒介从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渠道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成为了社会生活重构的设计者,媒介逻辑重构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未来传播学科研究的重点将不仅仅在于内容,更在于研究传播如何重构社会生活,即在非内容领域发展和重构传播的角色、作用机制及发展模式等等。
在社会“媒介化”进程中,非理性已成为传播机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性因素,“破圈”传播与沟通已成为社会发展之于传播最为重要的责任与使命;另外,还要看到数据和算法的“霸权者”影响,在未来传播中,数据将成为传播产品的“标配”;此外,传播内容生产的主体正在经历着从专业化到精英化,再到“泛众化加智能化”的改变。在这种情形下,专业媒体与专业传播工作者应由直接的内容生产者To C转型为To B的角色,成为数据与算法的掌握者、服务于大众的传播模板与技术的提供者、新传播领域与传播形态的开发者、全社会传播中信息、意见与情绪的整体平衡者。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黄旦教授从媒介变迁的视角分享了他对于“后真相”这一概念的思考。在黄旦看来,在数字移动传播的背景下,所谓的“后真相”得以萌生。“后真相”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即“媒介/传播的真实性”——“陈述之真”。就其性质而言,“真相”与“后真相”并不是何者更真实的问题,而是真相的陈述发生了变化,背后是“人-媒介-现实”关系的变化,不同媒介造就了不同真实。因此,研究“后真相”,应研究媒介变迁与“陈述之真”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真实感知变化。
数字移动传播之所以带来了“后真相”,是因为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媒介不同的“尺度”,导致我们认识真相的不同方式:“把关”是大众媒介的隐喻,其是标准和统一化的,形成了具有专业性和封闭性的“新闻业”这一新社会传播形态;与之相对,“流动”是移动媒介的隐喻,形成了以共享为规则的观看文化,以及“千手观音”式的众生新闻。由此,“复眼之真”/“彩虹之真”与“雷达之真”/“探照灯之真”不同。因此,我们不能以“印刷-中央媒介”所形成的“真实”文化来衡量数字媒介,而要在数字移动媒介的尺度中,去探究数字化时代的“真相”所具有的特点及其构成,确立新的标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援引芒福德归纳了人类文明的两个表征——媒介与城市,前者对应想象空间,后者对应实体空间,二者相互转化和映照,共同实现对人类文明的储存、流转和创造。人类文明历经了四次工业革命,走过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当前正在进入以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智能时代。依照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的观点,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生活方式。人类社会也正在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迈向都市社会,逐步实现人类社会完全的都市化。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大众媒介时代,城市的核心问题在于“分裂的整合”,大众媒介通过制造共识建构共同文化。而在智能时代,城市的核心问题是“共在的沟通”,智能媒体的作用是“见证差异化的共在”,城市文化也从“共同体”走向了“共通体”,媒介想象空间和城市实体空间交织、融合,形成了人类第三种空间形态——“虚拟实在”。未来,都市组织由智能系统所支撑,个体日常生活由移动终端所中介,人类形成依存而非整合的共在感,人类文明将最终形成以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网络——卡斯特所言的“都市星球”。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教授将目光聚焦到互联网平台。他指出,平台社会是当前网络化社会最典型的表现,媒体融合、舆论研究等研究继续深入都会不约而同汇聚到平台研究上来。包括腾讯、阿里巴巴、抖音在内的数字互联网平台,已经或正在成为我们社会的底层基础设施。这一方面是由于平台契合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社交、交易、消费、娱乐等根本需求,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数据捕获、算法推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发展。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平台不是一般意义上作为内容聚合容器的平台,而是通过数据捕获和算法推荐、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建立起社会连接的底层架构。张志安也指出,技术并不是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唯一动力,平台基础设施化是一个技术、权力、商业在社会中展开互动博弈的复杂过程,按照欧洲学者的概括,数据化、商品化、选择性是互联网平台运作的重要机制。
张志安认为,当前围绕互联网平台治理,大致有8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和方向,包括:平台与数据隐私权、平台与资本监控主义、平台与数字劳动、平台与算法推荐、互联网平台的垄断、平台与政治干预以及平台兴起与新闻业变革。他认为布厄迪厄的场域理论能够成为我们分析平台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研究者可以在了解不同类型互联网平台行动者距离权力核心位置的基础上去细致考察资本的转换的行动者惯性的生成,并在过程性的研究中扩展学术视野。在平台的公共性问题上,张志安认为,区别于大众传播媒介时代基于专业媒体把关功能的公共性逻辑,公众共同参与是平台公共性的重要特点,因而今天我们需要在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当中,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去讨论和理解平台的公共性问题。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李良荣教授同样关注到互联网平台在当下所呈现的双重属性:私有制与公共性。李良荣指出,从美国到中国,由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性地位所引发的网络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核心关注。新冠疫情更是让每个人意识到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地位无可撼动、无可替代。经过多年艰难探索,互联网平台公司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成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权力主体,与公众、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互联网平台具有双重属性:其一,平台作为私有制主体,以盈利为根本目的,只有通过市场垄断才能保障高额技术研发投入的市场回报率;其二,平台作为社会基础性设施,政府和社会要求其践行公共性,落实平台主体责任,承担技术安全评估与预判、用户注册与信息保护、信息发布审核、信息安全管理、风险应急处置、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未成年人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职责。但我们必须正视,过重的主体责任要求平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份,让互联网平台公司难以承受公共性之重,需要引入新的制衡力量,才能缓解私有制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优化网络治理模式。
与主张对互联网平台业务进行结构性拆分和主张将其国有化的两种方案不同,李良荣提出以“私有制属性,社会化监管”为核心理念的第三种方案,即设立由政府代表、平台公司代表、社会各界代表共同组成“互联网平台治理委员会”,在维护董事会对平台内部管理决策权的前提下,对互联网平台可能有损公共性的涉外事务进行监管。这种方案强调既不能让资本决定一切,也不能剥夺平台公司的所有权。“互联网平台治理委员会”不是套在平台公司头上的“紧箍咒”,而是帮助互联网平台公司规避风险,缓解与政府、社会各方的矛盾,替互联网平台松绑、减负的新治理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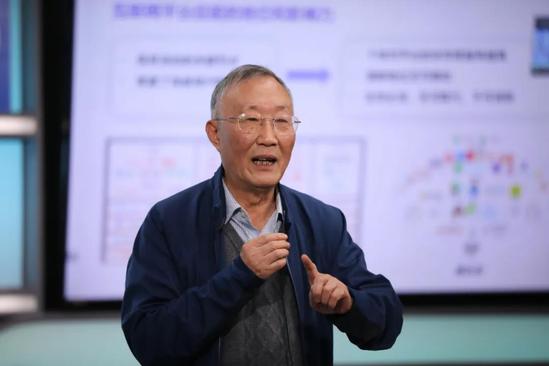
本届论坛线上线下同时举行,共有14000余人在线参与。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主任李良荣表示,“通过今天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创新的无限可能性,我们希望新闻传播学在互联网的研究上有更多的新观点、新见解出现,能够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创新的氛围。这就是我今天举办这个论坛的基本目的。”
*感谢袁鸣徽、曾培伦、周玉桥、魏新警、辛艳艳同学的文字整理